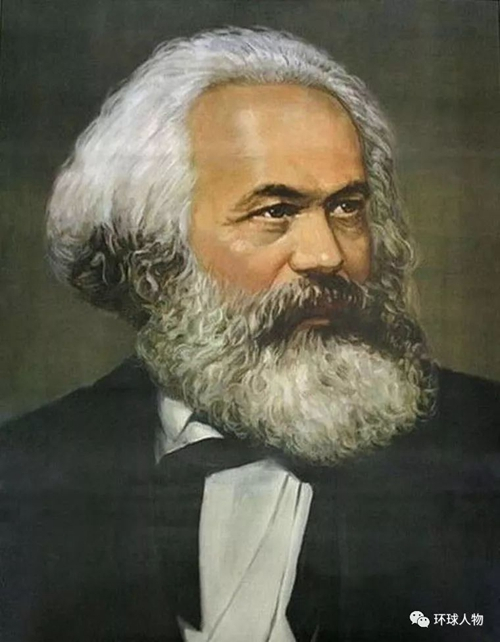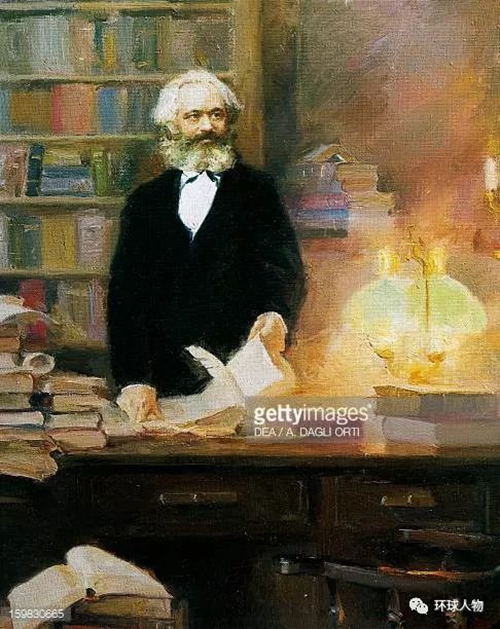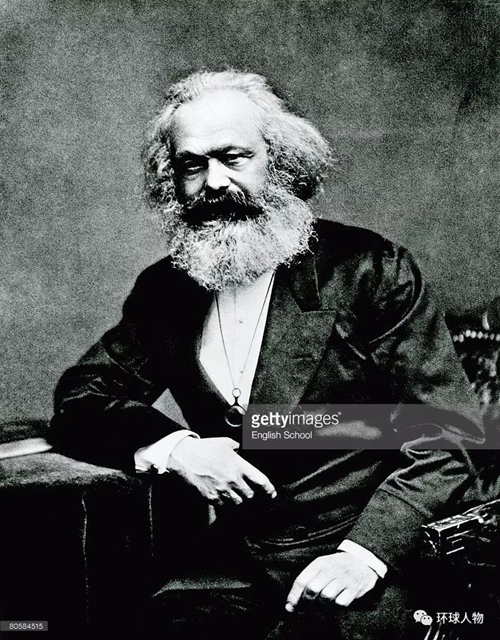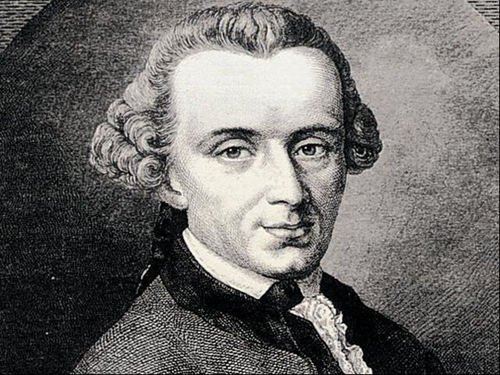17岁的一天,马克思走入学校,交上了自己的中学毕业论文。虽然与身边的同学相比,他的面容稚气许多,但眼神坚定而自信。几天后,这篇论文到了马克思的历史老师、学校校长胡果·维滕巴赫的手中。他仔细读完文章,在空白处批阅道:“非常好。”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近200年后,人们依然熟知、甚至依然能背诵的那段话便出自此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17岁的马克思神采飞扬地为自己写下了未来的路。崇拜者从这个起点开始讴歌他的高尚,异见者从这个起点开始腹诽他在唱高调。“高尚也好,高调也罢,重要的是,他后来确实是如此践行的。他就是把职业当成了事业,他就是把高调唱成了高尚。”《马克思靠谱》一书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钟君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道。
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特里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很有意思的是,如果用今天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年轻人的价值观来衡量,马克思简直就是那个“我们奋斗半辈子想要成为的年轻人”“出生在终点的孩子”——他的父亲亨利希是犹太人,在高级诉讼法庭担任法律顾问,多年来一直是特里尔律师协会的主席,很受当地人的尊敬。后世学者通过他们家缴纳特别税的金额推断,马克思一家属于特里尔前5%的高收入人群,位于金字塔的尖端。典型的中产阶级画像。
马克思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前面有一兄一姐,但在他出生后不久,哥哥夭折了,他成了家中的长子。后来他又有了2个弟弟和4个妹妹。在姐妹们的回忆中,马克思顽皮起来会“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山坡上“驱赶下来”,会用脏手拿着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蛋糕”喂给她们吃。但聪明的马克思,总会在恶作剧后讲述动人的故事,让姐妹们不至于真的生气。这又是当代年轻人朋友圈里艳羡的中产阶级标配:不独生,两孩以上,作伴长大。
马克思的成长方式,更是现在被奉为圭臬的那一套中产阶级理念:爱与自由。在现存马克思与父母的通信中,他的父母写得最多的是“我爱你胜过一切”“有了你,我已心满意足”“永远像你父亲爱你那样爱你的父亲”……马克思从家庭中收获的是丰盈的爱,于是得以无忧无虑,放纵着天性,自由地生长。他的父亲,就像大家所设想的律师们一样,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家中的庭院、楼上的书房里,年幼的马克思都曾被父亲抱在怀里,听他念诵法国作家伏尔泰和拉辛的作品。等到马克思12岁,就被送进当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特里尔这座城市很特别,在马克思出生之前,拿破仑战争时期,它被划归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里尔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契约自由、民事权利平等、保护私有财产的宽松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在马克思出生前4年,特里尔回归普鲁士,但这里依旧是德国自由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区。
所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感受到了从18世纪启蒙运动延续下来的自由主义精神。自由,成了埋入他心中的第一颗种子。他在校期间,校长维滕巴赫参加了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大游行,引来了警察搜查学校,结果从学生的物品中发现了讽刺普鲁士政府的文学作品。后来,马克思的数学老师被指责信仰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则被训斥不该唱革命歌曲。在这所自由主义的学校里,只有副校长反对自由。马克思的态度是——在离开学校时,他向所有老师辞别,但唯独没有理睬副校长。
在完成那篇论文后不久,1835年10月的一天,马克思凌晨4点就起了床。这一天,他将离开温暖的家、离开熟悉的特里尔,前往波恩读大学。全家人一起出动,到汽船码头送他离开。这是他人生中首次离家远行,结果成了终生的远行。
他遇到了老校长黑格尔
在成为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那个马克思之前,他也曾是叛逆的青年。初到波恩,马克思就被那里盛行的浪漫主义感染了,差点成为一个诗人——虽然子承父业就读法律系,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诗歌创作上。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高昂激越、如“汪洋大海里跳跃着的波涛”一般的文字风格,不知是否来自于此。但在当时,他沉迷于写诗只能增添父亲的烦恼,“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
马克思让父亲烦恼的可不只是不务正业。在波恩大学的第一学期,他经同寝室的老乡介绍,加入了特里尔同乡会,并很快成为5名领导者之一。这个同乡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喝酒。许多个夜晚,马克思与会员们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借酒吵闹。寄回家的账单更是表明,那时的马克思格外放纵自己的欲望——他在一年里花掉了700塔勒(当时的一种银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的富家公子一年也不过花掉500塔勒。按照购买力来算,700塔勒相当于现在的14万元人民币。这一切终于促使父亲安排马克思转学去柏林大学,而这成为马克思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之一。”钟君说。
柏林大学的面积是波恩大学的3倍,但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氛围。有柏林大学的学生在信中这样形容:“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这里这样普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兴趣,这样向往学问,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馆。”马克思很快被柏林大学的学风所影响,开始“野马收心”专心于学术研究,不仅认认真真读起法学功课,还爱上了哲学。伊曼努尔·康德成了他的第一位导师。
在马克思出生之前,康德就去世了。不过即便在世,两人应该也难以发生交集。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一辈子都过着单调的学者生活,至死未踏出过出生地柯尼斯堡。康德在一座城市停留了一生,但他的精神世界没有边界:“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
伊曼努尔·康德
或许正是这样浪漫的精神世界吸引了马克思。来到柏林大学的第一年,马克思就雄心勃勃地试图创造一种抽象法哲学体系,“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他洋洋洒洒写了300多页的书稿,却越写越苦闷,压根儿没法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出现了一条横跨在抽象体系和具体问题之间的巨大鸿沟。钟君解释道:“康德的思想系统自成一派,其中核心的三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被合称为‘三大批判’。这都是对马克思启发很大的部分。但马克思渐渐发现,康德太务虚了,总像是在做数学题目,用一个原理来证明另外一个原理,那么抽象的原理和具体的事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没有答案。这成了马克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时,马克思已经因为通宵达旦的学习和沉重的精神压力病倒了。医生建议他换换环境,于是他去了柏林附近的斯特拉劳小村庄休养。绿树清波、鸟鸣犬吠,都无法缓解马克思的烦恼,结果是黑格尔救了他。
黑格尔曾是柏林大学的校长,不过在马克思入校之前,他就已病逝于任上。马克思很早就读过老校长的一些文章片段,却“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这回养病,他不仅“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终于“诱入敌人的怀抱”。
黑格尔
在写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如此形容这次思想上的蜕变:“就像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在钟君看来,黑格尔吸引马克思依靠的两大秘密武器:一是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二是貌似强大的概念辩证法。“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事物不是静止的,是变动的。”最终,马克思的“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
那些人人艳羡的、他生而拥有的东西,自此退场了。
“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
1838年5月,20岁的马克思收到了父亲亨利希去世的消息。在去世前不久,亨利希还写信表达了对马克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踟躇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的忧心忡忡,迫切地希望马克思不要“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他不能理解儿子天才大脑里的思考,但仍以深沉的父爱为儿子提供经济上的雄厚支持,让马克思免于生计烦忧。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父亲的热爱,一直贴身带着父亲的一张照片,但他从来都不把照片拿给陌生人看,“因为它已经很不像原来的样子了”。
亨利希的去世导致马克思家的收入大大减少,在毕业后尽快找到一份工作成了马克思的当务之急。1842年10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24岁的他有了第一份稳定的工作——《莱茵报》主编。不,更准确地说,他第一次走出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第一次离开了悬浮于半空的象牙塔,看见了贫困的底层民众。
当时,莱茵省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名叫《林木盗窃法》的新法案。这项新法案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到森林里捡枯枝来生火做饭、维持生计的人,因为在土地私有者看来,未经允许私自捡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盗窃。“黑格尔提出过一个‘绝对理念’,即绝对化和神化人的理性。这其实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眼中,国家和法律就是这种绝对理念的化身,普鲁士政府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国家’,永远坚持公平和正义,永远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严酷的现实,让马克思从‘天国’回到了‘人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陈培永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面对省议会和土地私有者的步步紧逼,年轻气盛的马克思挺身而出,为保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脏”。陈培永感慨道:“正是在积极参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并清醒地认识到,普鲁士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什么‘理想国家’。这动摇了他对黑格尔的信仰。”
《莱茵报》在马克思手中变得极具活力与攻击力。该报的一位撰稿人曾这样描写道:“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或者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扬名全国,发行量比原来多了一倍多。这很快得罪了利益集团,马克思不得不辞去《莱茵报》主编一职。
失业的马克思转头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与燕妮结婚,接着准备去巴黎和同伴一起创办刊物《德法年鉴》,最后他给幽居乡间的费尔巴哈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为《德法年鉴》创刊号写一篇文章。为什么是费尔巴哈呢?因为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感到失望时,恰好收到朋友寄来的一篇费尔巴哈的文章《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这让他“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
燕妮与马克思
费尔巴哈曾是黑格尔的学生,可以说和马克思是师兄弟关系。只不过这位师兄早早就背离了老师的观点,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不是存在来自精神,而是精神来自存在。他的思想成果使得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被完全颠倒过来。
可是费尔巴哈没有接受这个小师弟的邀请。他长期住在幽静的乡村,集中精神思考问题,是个精神上的离群独处者。热情的马克思独自向前。“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学会了唯物论。但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并没有迷信权威,反而汲取了黑格尔的精华和费尔巴哈的精华,进行了改造,最终形成了唯物辩证法。”钟君说。
1845年,以《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为标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基本形成,揭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据此得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基础上,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作者:郑心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