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段志强在上海崇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许晓迪/摄)
段志强
1980年生于河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网络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系列节目撰稿人之一、转述人,《白银时代旅行史》主讲人。

段志强在院子里劳作。
5月,崇明岛向化镇花仓村村民段志强家喜添新丁,屋檐下一窝小燕子,嗷嗷待哺。
快到饭点,他拿着不锈钢盆进了菜地,砍了一棵老芹菜,准备炒点猪肉;割了一小把韭菜,用来炒鸡蛋;又掐了几片叶子,气味像八角,是网购的贵州作物,可以冒充大料。邻居送来一盆蚕豆,他打算按本地吃法,做葱油蚕豆。“昨天看唐鲁孙在书里写,上海人真爱吃蚕豆,菜场外的蚕豆荚堆得像小山。”明年,他打算也种点。
这是段志强开始种地的第三个年头。2022年初,他和家人搬离上海市区,“退出房地产游戏”,住进崇明一栋三层农房里,租金一年4万,前厅硕大的玻璃吊灯,闪耀着乡土的奢华。屋外有几块地,种了二十来种作物,有的长势喜人,有的形容枯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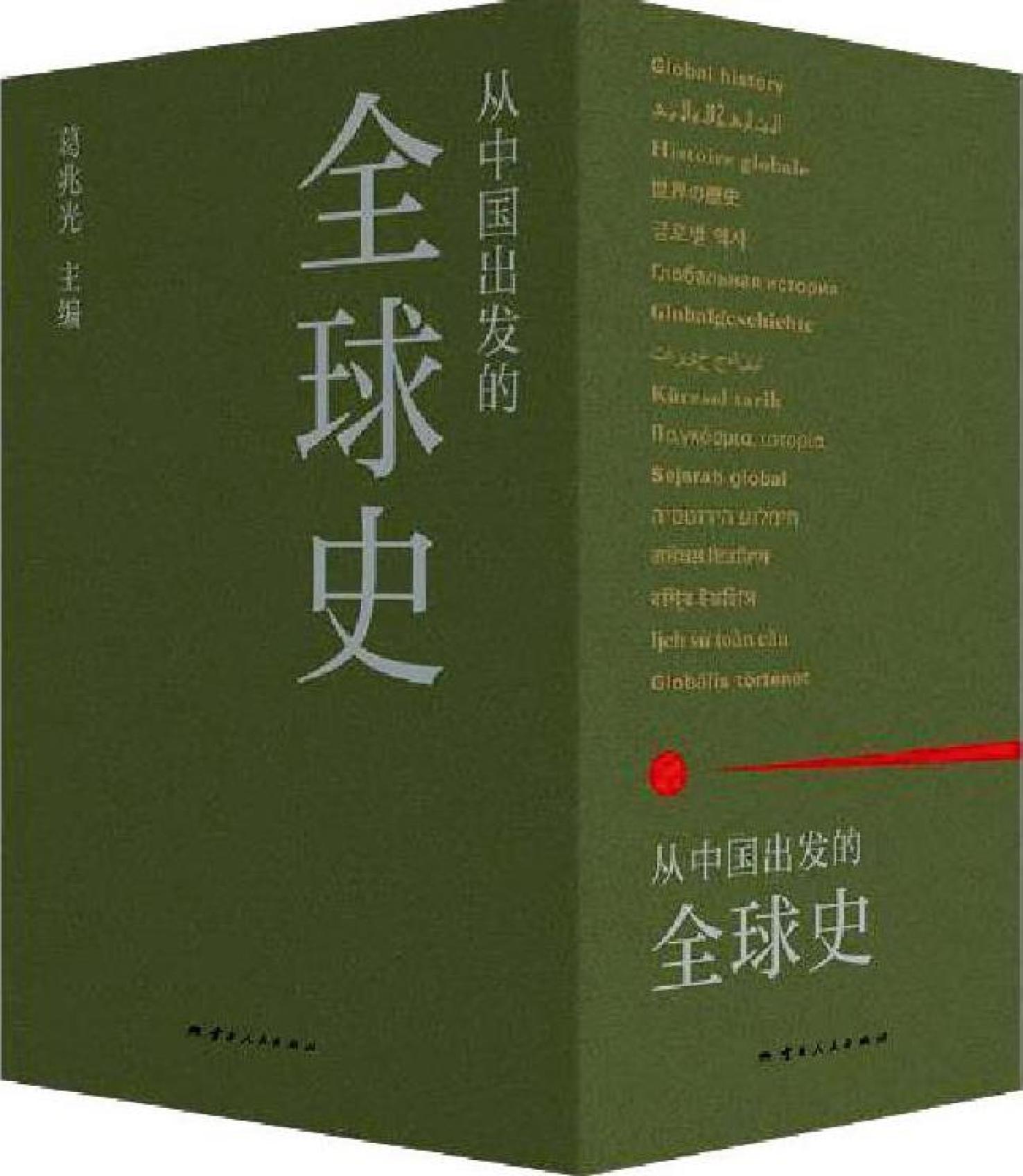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全三册)。
而阁楼之上,是另一个劳动天地——一个历史学者的知识生产车间。作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在学校上课,也在线上平台开课。不久前,三卷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出版,脱胎于在“看理想”连载两年半的同名播客节目。节目做了六季,集合了二十几位新生代学者,解读跨越300万年的全球历史图谱。
作为节目的撰稿人之一,同时也是贯穿始终的转述人,段志强让这档原本很可能板着脸的“高大上”节目,多了几分趣味和幽默。众多听友表白其“迷人的嗓音”与“让人专心听下去、听完又不觉得累的讲话技术”,“声优”界的一颗新星,自此冉冉升起。
一个“历史声优”的自我修养
段志强的“历史声优”之路,是被导师葛兆光拉上道的。
2018年,葛兆光和“看理想”总策划梁文道在上海见面,提议做一档全球史播客,一周后,一份6000字的详尽大纲交上。在葛兆光看来,全球史不同于《史记》《汉书》这类王朝史和英国史、日本史这类国别史,也区别于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要讲的,是一种超越国境限制,联系的、互动的、交往的历史;一种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没有中心”的历史;一种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问题和视角去看全球的历史;一种充满故事和细节,既追述人——从南方古猿、部落首领到旅行家、传教士,也观照物——从小麦、辣椒到茶叶、白银的历史……
“全球史”从头说,战争与移民,商品贸易与物质交换,宗教与信仰,疾病、气候与环境,大航海之后,六大主题下,20多位撰稿人集聚。葛兆光邀段志强加入,一向“爱凑热闹”的他欣然入伙。第一季节目一共五讲,他写了其中四讲,拿出备课的热情,边学边写,乐在其中。
文稿推动了,声音又是难题。每位作者都“出镜”,众声喧哗,听众迷糊;请专业声优,照本宣科没感情。编辑想起一向热情又风趣的段志强,给他一段稿子试音,念了两遍后,就是这个声音了。
在北京的录音棚里,段志强完成了第一次录制,此后的节目都在家里完成。有一次在云南永平,他和队友失联,在竹林躲雨,无所事事,就录了一段“番外”。雨水打在伞上滴答作响,旁边小河流水淙淙,大自然的白噪音里,他从一道黄焖鸡讲到博南古道的历史,类似今日“司机快餐”的马帮菜,以及辣椒、土豆、玉米等美洲作物在中国西南山区的传播,“其实只要你留意的话,我们身边看似很寻常的东西,也都有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是段志强第一次参与音频节目。在此之前,他不听播客,只听评书,喜欢袁阔成、王玥波。说书人擅长用声音控制氛围,他想自己的“声优”天赋,或许偷师于此。
而从各位作者那里“偷师”各种知识干货,也是这趟全球史之旅的重要收获。“我们总觉得历史属于文科,但真实的世界其实容纳了各种知识门类。为什么历史学家总喜欢讲那些勾心斗角的政治权谋?因为别的都不懂:不会打仗,不会种地,不会开船,不会做生意……地图的文化意义讲得天花乱坠,但一张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有哪些测绘技术?一句蒙古人勇猛善战,好像南宋活该亡国,但蒙古人如何射箭?骑在马上还是跳下马来?不同的战争模式导致不同的历史结局。《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要探讨的,就是这些具体、细节、硬核的问题。”
第二季之后,除个别情况需代班写稿,大部分时间,段志强是专职“声优”,将不同文稿“据为己有”,加工改造,“脑子里塞满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我现在练就了一种在前辈学者看来非常糟糕的技能,不管和什么人都能聊上两句,变成一个万金油式的存在。”他觉得这样也不错,“阴差阳错变成这样的人,就好好享受。”
“但是没有我的猫享受。”此刻的“老马”——女儿喜欢京剧,给家猫赐名“马连良”——沐浴在阳光中,风从天窗涌进阁楼。这是一年中的舒服时刻,段志强说,到了盛夏,满屋蒸腾着松木气味,那3个月,他只能从这闷热的温室撤退。
“历史能小一点,个人能大一点”
“我可能是我们这一行最不务正业的人。”段志强说,以从事职业工种的丰富度而言,确实如此。
生于1980年,段志强亲历过“上岸”又“下海”的时代浪潮。从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他回到老家,在人事局做了4年公务员。想象中喝茶看报的清闲并没出现,挣得少、工作忙。2006年,他决定考研,选了“不赚钱”的历史学。
2013年,段志强博士毕业,留在复旦任教,生存压力倍增。他在小区附近租了两家店面,一家奶茶店,一家馄饨店,前者开黄了,后者还活着。钱没怎么挣着,最开心的事是坐在店里和人聊天,成功打入老太太和小商贩们的生活世界。
这些“正业”之外的旁枝逸出,让他跑偏于历史学的正统框架,走出一条“野路子”。“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往往从概念出发,将其作为观察世界的重要武器。我因为武器掌握得不好,更喜欢从生活本身出发去思考问题。古人没读过博士学位,不是按现在教授学者的思维方式去行动的。这些思维方式是理性的,往往是掌握了大量事实、经过了精密计算后做出的选择。但那个真实置身历史现场的人,一定不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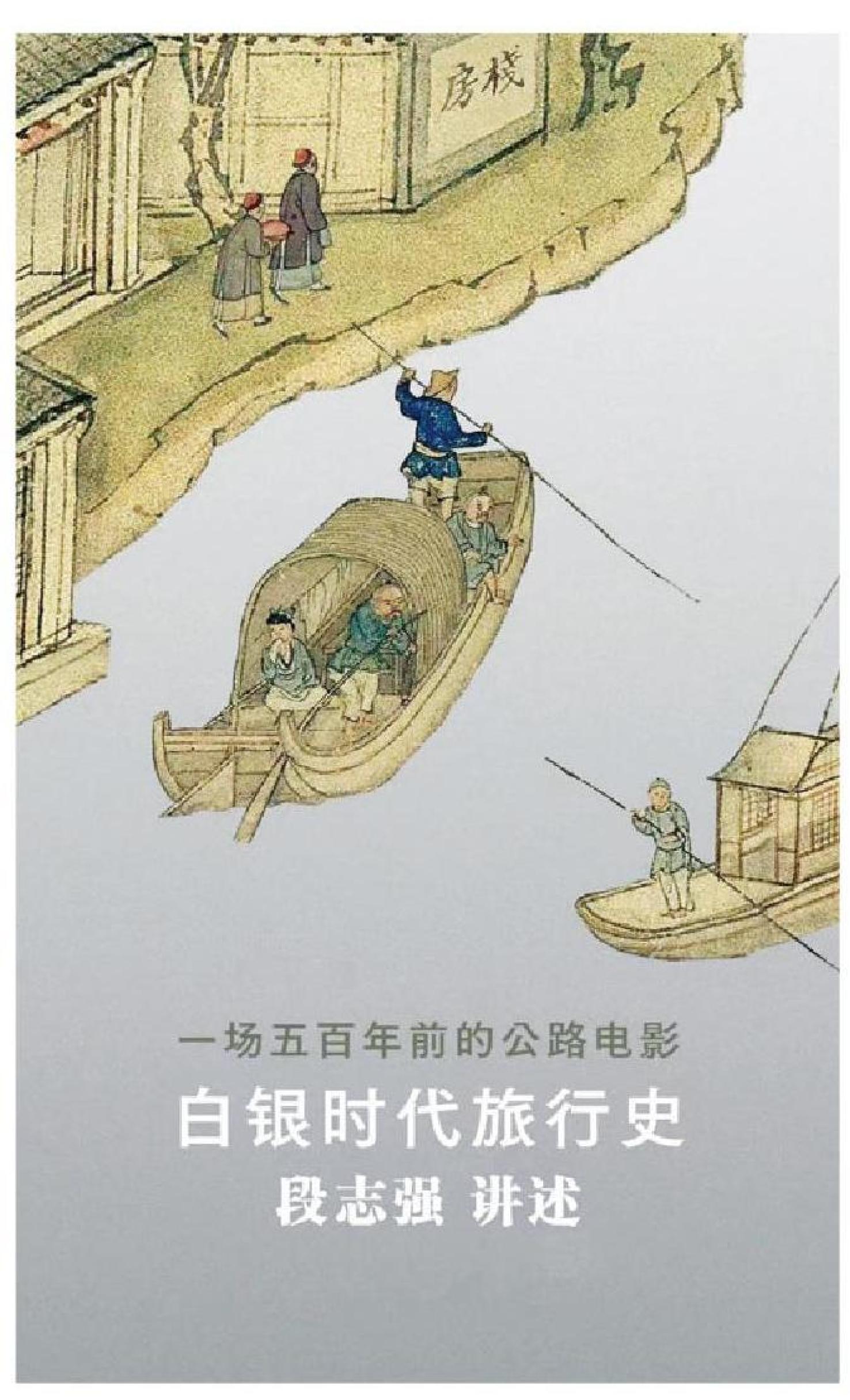
音频节目《白银时代旅行史》封面。

清代《姑苏繁华图》(局部),表现了“白银时代”古城苏州的实景风貌。
2023年4月,音频节目《白银时代旅行史》上线。段志强聚焦于明代中叶至清代末期的“大旅行时代”,讲男女老少、士农工商们各怀心事与梦想出门上路的故事。“我们会努力在个人生活中触摸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理解个人命运。”在发刊词中,他写道。
离开大人物的探照灯,《白银时代旅行史》里登场的都是时代巨变里的普通人:有人赴任调动,就有人贬官流放;有人赴京赶考,就有人落榜回乡;有人长途结婚,有人万里寻亲;有人修仙求道,有人探险壮游;商人的车队穿梭往来,办案的差役行色匆匆,看风水的先生走南闯北,使臣的大船漂洋过海……“自下而上的历史也好,从生活出发的历史也好,所有历史学者都同意,但原则上认可而不付诸实践,这些概念也只是一种灵感的口号。”真正要做的,是去未被照亮的历史地图中挖掘,“也许挖出的东西,对一个学术生产者来说没什么用,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当你被它所触动,它就会成为你生命的养料”。
段志强讲起最近研究的一群清代徽州的数学发烧友,“和吟风弄月的传统文人很不一样,整天研究的是三角函数、球面几何”。在一位数学家的著作里,每卷开头都有文字记叙,不乏真情流露:去年乡试落榜,朋友看我难受,出了这道题给我做,我没心情,扔在一边。今年朋友的小儿子去世了,我拿出旧题,解出来给他排解郁闷;被大雨困在乡间小店,想朋友,不知道他想不想我,再做个题吧……“我读着很感动,这就是我生命的养料,讲起来就特别开心。”
听众的评论,也是一种“养料”。段志强不喜欢“科普”这样的词,带着自上而下的“语言暴力”,他更愿意将节目看作一次知识的交换和流通,“普及多吃亏啊,分享才能收支平衡”。《白银时代旅行史》的评论区,听众留下各自的旅行见闻。有人难忘儿时在夜航船上看到的月亮和江水,有人吐槽绿皮车时代的“人在囧途”,有老海员怀念水手生活,有美术师追忆勘景之旅。“你总会默认留言的都是同龄人,结果有一天蹦出一条:70年代,我到某地出差——啊,是位老大哥。”
“每个人都是‘野生’历史学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叙述一个大时代。”段志强说,“我希望历史能小一点,个人能大一点。有人喜欢与潮流共振的宏大感,有人追求超越性的东西,有人容易被花花草草打动,有人喜欢和钱共情。所有人都有自由生长的机会,我学历史,特别怕历史成为一种枷锁。历史是启发我们的,不是规定我们的。”
“去种两年地,就知道啥叫不确定性了”
到乡下种地,对段志强来说,也是个人生命的生长。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巅峰,就是小时候在河南老家和爷爷生活那会儿。村里有座避洪水的高台,爷爷在上面种了葡萄、黄花菜和各种各样的花,在四棵梧桐树中间搭了一张悬空的床,到了晚上,他就坐在这空中花床上,欣赏月光下的村庄。
搬到崇明后,有一天他一边烧火,一边和老婆说:“你看咱们辛辛苦苦几十年,终于过上小时候的生活了。”
在大学那个被“保护”的小气候里,体验世界也不那么生动。自从住到村里,他又重新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会刮风下雨,有春露秋霜,一场大风可能干掉一半收成,半天透雨又能节省一月水费。第一年,他种了甜瓜,好吃到消解了搬家的所有折腾,飘飘欲仙;第二年,他决定多种点,可以拿出去和村民搞搞关系,结果夏天雨下不停,一个也没长成。今年,他又种了甜瓜,再不敢踌躇满志、到处宣扬了。“大家天天喊,生活开始变得不确定了。我说你去种两年地,就知道啥叫不确定性了。”
今年种猕猴桃,段志强犯了致命错误,猕猴桃是雌雄异株,他却买了两棵母树,一直想偷别家一朵雄花,最终没成功,只能幽怨叹气。桃子倒是长势不错,他依旧忐忑,“跟看女儿一样,越长大越漂亮,一方面开心,一方面紧张”。对面蔬菜基地的大棚里,已结了不少小西瓜,他想起去年自家那个唯一的小家伙,一场雨后,炸了。
尽管常有“农夫心内如汤煮”的煎熬,但任性的土地也常给予丰厚的馈赠。去年的红薯,现在还没吃完。胡萝卜只种了两平方米,朋友来了挖走不少,他一箱箱地往外寄,顿顿吃,还是消耗不完,最后腌了咸菜,一罐一罐堆在厨房。
在他看来,“种地和做学术,本质都是劳动,光瞎想,不干活,就啥也没有”。不同的是,体力劳动比较开心。“论文,很长时间发一篇;书,几年出不了一本。但我站在地里,每天都有收获,内心很充实。今天芦笋冒芽了,明天黄瓜长大了,地里20多种作物,这个不收那个收,啥都没有,就割一茬韭菜。邻居送来一盆蚕豆,我让他们挖点生菜移栽。不开心的事照样有,但开心的事多了,生活就平衡了。人生需要正向反馈,纯粹靠内心强大来应对生活,是空手套白狼,对自己挺残忍的。”
这一天,段志强开上他拉风的电三轮,去镇上买新锄头。路边的野花丛丛簇簇,嫩黄的花蕊,细弱的白色花瓣。他说,这花叫飞蓬,原产于北美洲,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开始了世界各地的奇幻漂流,“又是一个全球史课题”。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43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