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底,北京短暂地褪去潮热,天气舒爽。科幻作家、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江波从外地赶来参加一场活动——“匠心筑梦·焕新视界——中国科幻·国漫崛起”动画行业对谈。
一身运动装,一个双肩包,江波没有舟车劳顿的疲惫感,关于科幻的一切话题他都能聊得生动、深入,有问必答,保持开放。江波是典型的“理工男”,2003年,他从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同年发表了首作《最后的游戏》,后陆续发表《移魂有术》《湿婆之舞》《随风而逝》等众多中短篇小说。2012年开始创作长篇科幻文学,历时4年写出《银河之心》三部曲,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展现了巨大时空尺度下的太空世界,获得第28届银河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同名动漫改编作品也在科幻迷中引发讨论。
一篇小说,一部电影,一部动漫,关于科幻作品的改编创作,关于未来世界,关于人工智能,活动间隙,他和记者聊了起来,身边不时有人拿着书请他签名,他对待读者非常热情。在江波看来,“说到底,关于创作的所有议题最后都要回归到人”。
以下,是江波和人民文娱记者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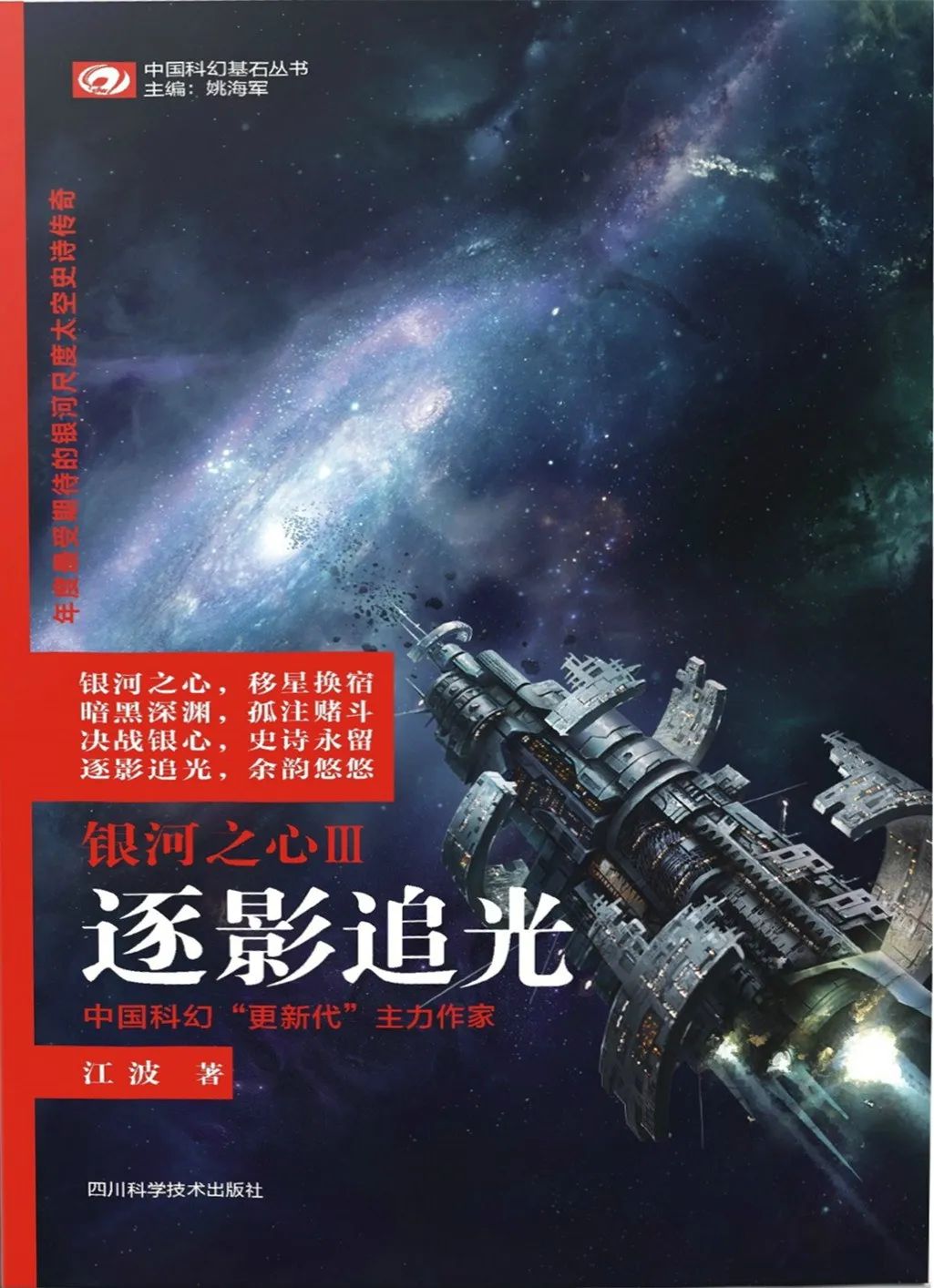
“尽量少去干扰他们的创作”
人民文娱:一直以来,包括科幻作品在内的文学作品影视化对创作者来说都是“惊险一跃”,在您看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江波:改编的成败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以我的经验来看,抛开原有IP本身的影响力不谈,主创人员是改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个好的主创团队必须抱有一种强烈的热情与投入感,这种自信和激情往往能够支撑他们走得比别人更长远一点,做得更好一点。
有时候,坚定的信念可能决定一个作品最后的命运。
科幻作品的影视化改编还要看留给创作者的空间有多大。如果一部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的叙事结构很好,是一个优质作品,这反而给改编者更大的创作空间。这就像,《三体》本身已经是现象级的文学IP了,加上它的世界观非常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很多设计、调整都要配合原著去做,过于大刀阔斧的改编反而不容易成功;反观《流浪地球》,少数读者可能读过这篇中篇科幻小说,而电影的成功才将其转变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IP,最后,电影反而脱离原著变成了这个IP的主干。

人民文娱:您的长篇科幻作品《银河之心》也被改编为动漫,您在改编过程中会着重强调作为原著作者的主体性吗?
江波:《银河之心》的动漫改编,和小说原本的故事线是有偏差的。在创作过程中,导演和编剧根据需要和经验自行把握,其实是一件好事。只不过,《银河之心》是长篇小说,即使是对细节的调整,也需要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把情节圆回来,所以改编难度很大。
影视创作的编剧环节会受到很多限制,是工业链条上的一环,并不像作者独立写作那么自由。我的原则是尽量少去干扰他们的创作,可以参加一些讨论,但不会深度干涉发展的结果。小说改编成了影视,融入了其他人的想法和努力,如果一定要别人遵从我的观点,那可能有点太霸道了。

人民文娱:您怎么看待影视化改编后“原著党”不买账的问题?
江波:这个事情见仁见智。像《冰与火之歌》改编剧《权利的游戏》,一些原著党的确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这部剧收获了更广泛的受众。
在我看来,影视化团队如果有足够的自信认为某种改编方式是好的,就应该按照自己的路子去走,作为创意行业,应该对观众的喜好与倾向有自己的判断。
换个角度想,“原著党”的讨论反而增加了作品本身的热度,这种争议其实是良性的,因为它是作品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竞争,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另一种形式的互动。

不必刻意强调中国元素
人民文娱:您如何看待如今中国科幻动画的发展?
江波:当前我国科幻动画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前所未有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所以电影、文学、动漫都会受到科幻元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动漫产业本身的进步。从之前《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这类古典水墨动漫的巅峰,后来有一段沉寂,到现在又重新辉煌。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漫题材扩展到科幻领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以及制作水准的提高,全球影响力的提升都是时代的必然。

人民文娱:不同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中国动画常常出现一种集体叙事,您怎么看待这种差异?
江波:每种文化都有一些核心理念,它们深刻渗透在人的思维当中,所以中国人做影视时也会不知不觉间展现这些理念。西方也有自己的特点,由于宗教的影响,他们的救世主情节非常强烈。但中国人自古推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叙事,这种差异是对价值体系的不同判断,价值观念并不是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的,而是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影视作品相当于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来阐述我们的观念,那这些观念能够影响多少人?我们的社会现实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命题其实是很大的,是一种社会工程性的问题。影视作品能够做的就是把这种理念通过作品潜移默化地传播给更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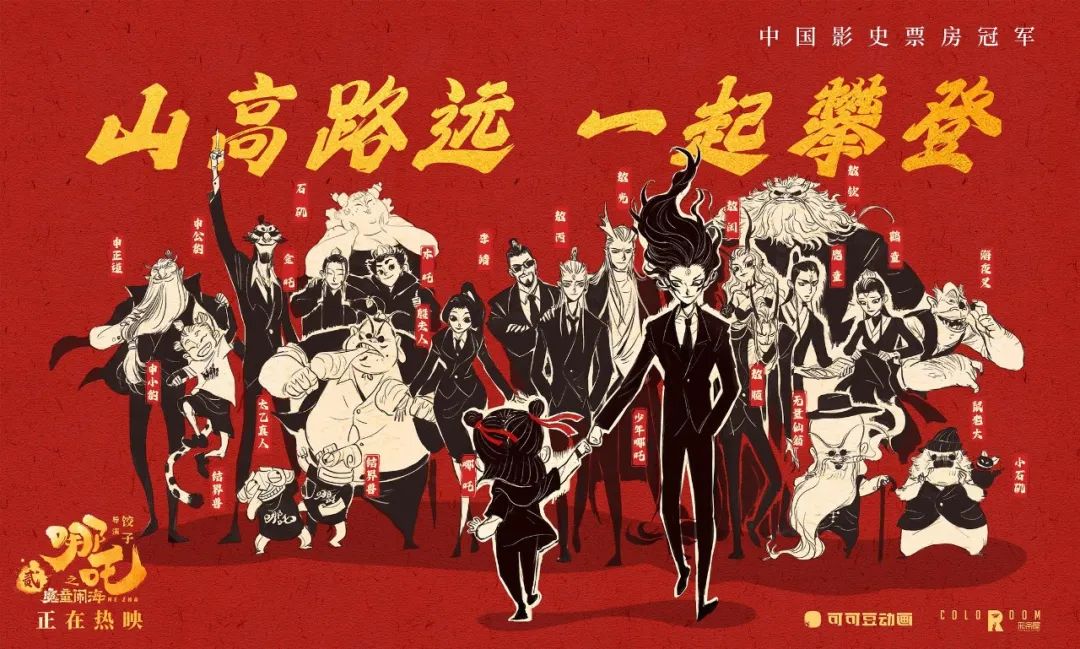
人民文娱: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科幻动画中有表达空间吗?
江波:在我看来,并不是只有山水田园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文化也要面向未来,结合现代科技。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时候,不能把目光局限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上,还可以看看我们当前有什么,我们能发展出什么,这才叫发扬中国文化。
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处于彼此影响、彼此交错的状态。科技本身就是跨国界的、流动的,世界的未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当中必然有中国元素的存在,但是不需要去刻意强调,因为我们中国人想象出来的未来,本身就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塑造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影响力。

太空为什么这么重要
人民文娱:谈到未来,您的作品《银河之心》也是讲未来的故事,在您截至目前的整个创作生涯中,这部作品有怎样的地位?
江波:我一直把《银河之心》三部曲当作自己的代表作。我的社交媒体头像就是“银河之心”4个字,它包含一种寓意——虽然你只是地球上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你的思想可以扩散到整个宇宙。
《银河之心》的架构非常宏大,不仅仅是这三部曲,还包括一些中短篇,还有一部《红石》。可以说,《银河之心》是我对银河史、宇宙史的想象。人类进入银河系太空旅行之后,人类文明发展到宇宙3级文明——根据苏联科学家卡尔达舍夫的划分,我们目前处在0.73级文明,3级文明指的是掌握了整个银河系的文明。这个过程是怎样的、那时人类是否仍然存在,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浪漫想象都在这部作品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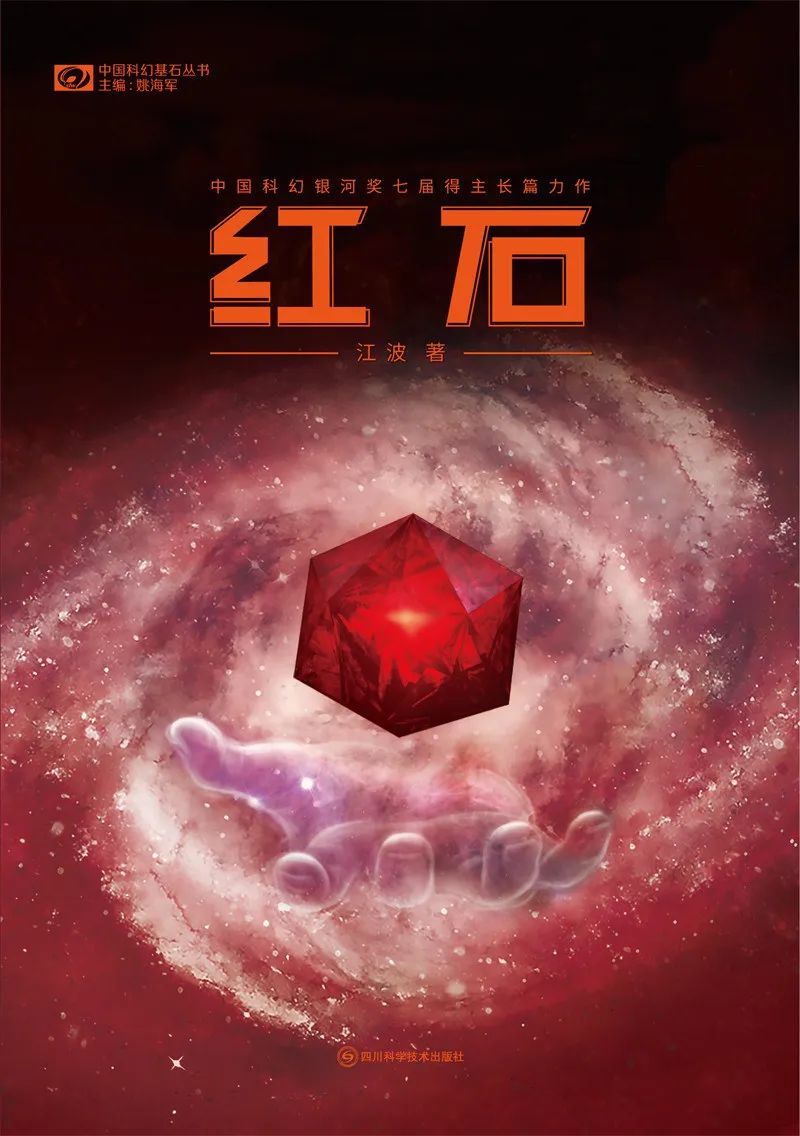
人民文娱:《银河之心》和您最早创作科幻文学的初衷是吻合的吗?在成长过程中,哪些科幻作品对您影响深远?
江波:我最早创作科幻小说的时候,作品主题就集中在太空探索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经典长篇小说《银河帝国》,它讲述的是,人类早已建成一个银河帝国,银河帝国怎样陷入混乱,这个混乱又怎样通过一些人科学理性的认知与方法平息了。它的疆域是整个银河,时间跨度以十万年甚至百万年为尺度,我写《银河之心》的时候也设定了这样的时空跨度。
我一直认为,作家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受到某种事物的启发,未来他在这个方面的兴趣会特别强烈。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科幻给我的印象就特别强烈。比如由美国金和声公司根据《超时空要塞》《超时空骑团》《机甲创世纪》3部日本动画重新剪辑改编而成的85集长篇电视科幻动画《太空堡垒》。它1990年被引进内地,当年我整天守在电视机前等更新。我还喜欢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他著名的作品《宇宙》《魔鬼出没的世界》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恰好也是太空题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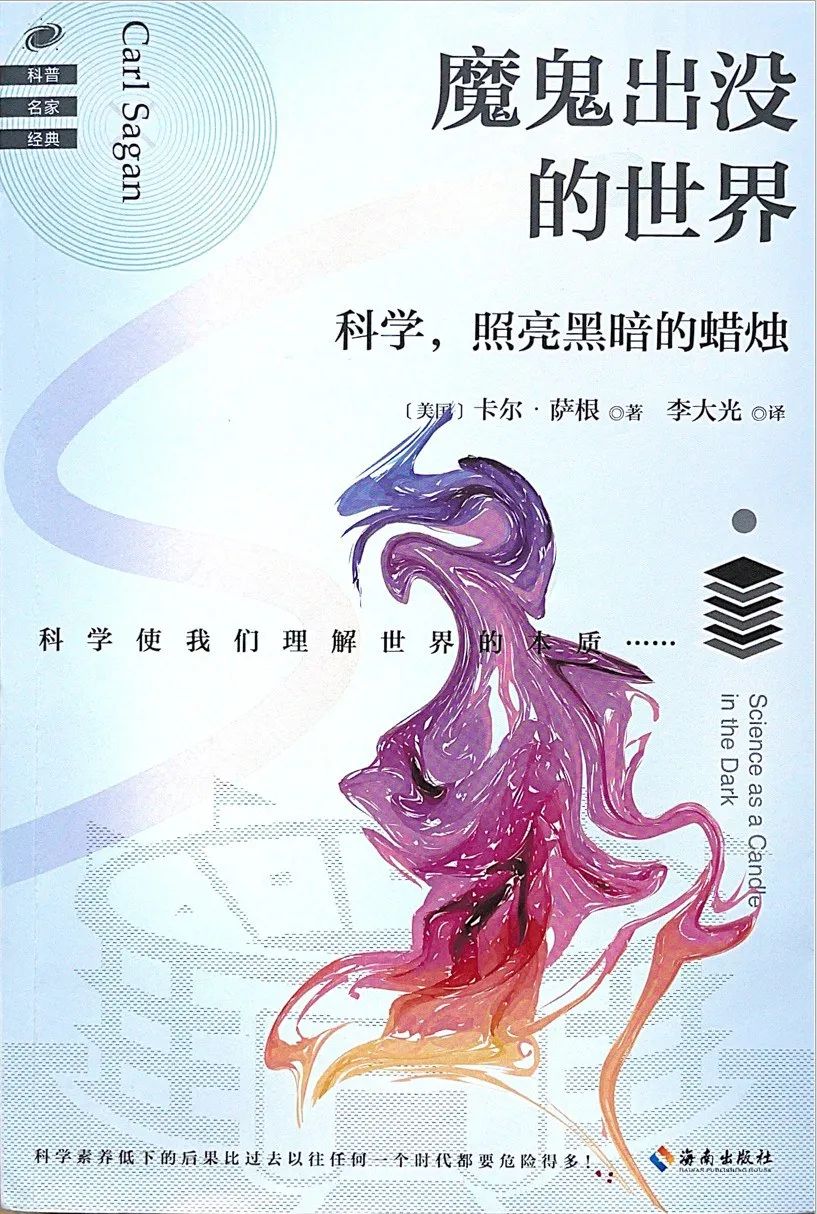
人民文娱:“太空”在您的创作中是不是具有特别的意义?
江波:太空为什么这么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广袤的太空来说,地球只是一粒宇宙尘埃。人类如果永远生活在地球上,其实是有点可怜的。所以在浪漫想象中,我们能从地球走出去,走向一个更加具有想象空间的未来——这是一种非常浪漫的、对人类未来抱着美好期待的想象。
我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一种延续,或者说人类的后代。太空虽然很广阔,但实际上不适合人类生存,所以将来可能是机器人带着人类的愿望,以他们自己的形态生活在太空中。
为什么太空在我的科幻创作当中占据重要地位?究其原因,我觉得它是人类的未来,只不过这个未来会跟人工智能深度捆绑在一起。
 责任编辑:邱小宸
责任编辑:邱小宸江波,《银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