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高世章,中国香港音乐剧及电影作曲家,纽约大学音乐剧创作硕士,代表作品包括音乐剧《四川好人》《雪狼湖》《钉头槌》等,曾为《如果·爱》《投名状》等电影配乐。2025年6月起,由其担任作曲、音乐总监的音乐剧《大状王》在上海、北京巡演。
22年前,身在美国的高世章接到一通电话——来自《雪狼湖》的制作人。《雪狼湖》是由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兼主演的音乐剧,1997年在中国香港首演便引发热潮。2003年,该剧开始普通话版本的创排,高世章受邀担任音乐总监。
“我本来想推掉,但是有朋友说一定要做。因为你应该体验一下音乐剧的商业制作,而不是在纯艺术里待着。”他对人民文娱记者回忆道。
2004年冬天,《雪狼湖》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连续6场公演,高世章第一次来北京工作。从机场坐车到少年宫排练,一下车风就从领口灌进身体,“太冷了”。演出还没开始,他就生病了。拖着病体彩排、演出,回到香港,他暗暗发誓:再也不要冬天来北京了。
不过,这趟旅行有个重要收获,高世章有了新的职业目标。《雪狼湖》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张学友的艺术魅力和明星光环。“那有没有可能,我就做一部‘戏抬人’的音乐剧?”
2025年夏天,高世章回到北京,带来了《大状王》,一部被许多媒体冠以粤语音乐剧“天花板”的作品。早在6月上海站首演时,该剧就一票难求。
7月11日,《大状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座无虚席,剩下9场的票很快售罄,临时又增加一场。20日,北京演出圆满落幕。

· 《大状王》作曲、音乐总监高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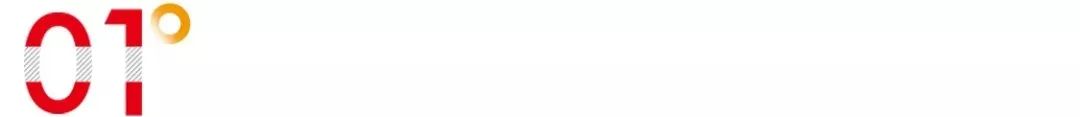
一部剧,近30种音乐类型
每次演出,高世章总喜欢待在控制室,一般是在观众席的一楼和二楼中间。在这里,他既能看到舞台上的每个角落,又能观察观众的反应。上半场结束,他就会趁着中场休息跑到后台,提醒演员下半场的细节。下半场开始,他又回到控制室,直到谢幕。
身处观众席中心,高世章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观众的反馈。各地笑点不同,喜欢的桥段和歌曲也不同,但哭点总是相似——不少观众,抱着看喜剧的心情走进剧场,最后哭完了一整包面纸。
这便是《大状王》在故事上的创新之处。方唐镜、宋世杰,剧中两位主角是周星驰电影《审死官》里的死对头,也是广东传统戏曲、民间传说中善恶两极的代表:前者是颠倒黑白、见钱眼开的讼棍“荒唐镜”;后者是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状王“讼师杰”。

· 电影《审死官》剧照。
这一次,方唐镜和宋世杰被“合二为一”,借由一段儿时意外和人鬼缠斗讲述了方唐镜成为宋世杰的觉醒故事。故事里有善恶因果的探讨,有亲情友情的呈现;有放下仇恨的解脱,也有蚍蜉撼树的勇气……
3场“公堂戏”是全剧演员调度最大、音乐运用最丰富的戏份,展现了方唐镜由恶向善的转折:第一场,他助纣为虐,帮恶霸打官司、害民女;第二场,他深陷“复仇诅咒”,逐渐良心发现;第三场,他与伙伴阿细北上为民请命,大义凛然。

·《大状王》剧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供图 )
第一场戏的音乐也是高世章最先创作的部分。“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开头,开场第一首就是《伸冤》。”他想象着公堂里混乱、紧张的氛围,脑中自动出现鼓点,写出了作为基石的16小节音乐。全剧作词岑伟宗根据音乐,为出场人物写出歌词:衙差、县官、佣人、富家公子……直到方唐镜上场,一句“收声、收声、收声”,第一幕进入高潮。

·《大状王》剧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供图 )
音乐制作上,高世章在这3场戏里融合了大量音乐类型,广东小调、击鼓音乐、滑稽音乐、南音甚至摇滚、歌剧,混搭出生动的市井群像和人物心理。20分钟的戏一气呵成,观众酣畅淋漓。
剧中还有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歌曲——《撒一场白米》。这是阿细放下对方唐镜的仇恨,与往事和解的独白。
撒白米是华南民俗,用于安抚亡魂,“骤眼告终就当撒一场白米”象征阿细的魂魄决定消散。创作这首歌时,高世章想到在朋友母亲葬礼上听到的佛教音乐,于是在开头加入《心经》的梵文吟唱,接下来粤曲、梵音、咏叹调,一首歌达到了既安静又揪心的效果。
对高世章而言,创作《大状王》的过程更像是在“玩音乐”,记者问他到底用了多少种音乐类型在一部剧里。他认真数了数——将近30种。

·《大状王》剧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供图 )

一杯咖啡碰出的“天花板”
2015年,高世章与岑伟宗在上海看剧,空闲时在淮海中路的一家咖啡馆闲聊。聊着聊着,岑伟宗突然灵光乍现:“你觉得《审死官》怎么样?”
高世章呆了一下。周星驰电影走红时,他正在美国读书,印象不深。反而是粤剧《审死官》让他颇感兴趣——将传统故事、地方戏曲、现代音乐创新表达,也一直是高世章想尝试的。

· 高世章(右)与岑伟宗合影。
很快,他们邀请编剧张飞帆加入创作。几个星期后,张飞帆给出了一份初稿,“除了故事中几个角色名跟《审死官》有点关系外,基本上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在香港音乐剧圈,高世章、岑伟宗是公认的黄金搭档,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高世章是理工科转音乐,天生理性,创作讲究起承转合、解构严谨,“我可以解释每一个段落为什么这么写”。
岑伟宗则细腻感性。高世章记得岑伟宗读到初稿中,孤魂阿细再次见到母亲的场景,“看着看着就哭了”。作词时,岑伟宗给自己定下要求:每段故事都要有语感层次。在他看来,粤语语感有6个层次:文、雅、妙、趣、俗、鄙。比如,剧中《悬崖》《撒一场白米》属于“雅”的表达;《福临门》里一段歌女演唱,遵循古腔粤曲写法,属“文”;紧接着的搞笑段落,每一句都是越唱越衰,趣味横生,通俗市侩。
初稿、作曲、作词、打磨,第一版完整的《大状王》花费了两年时间。排练开始前,高世章向作品委约方西九文化区提出想法:能不能按照工作坊的形式进行排练?“以前,香港音乐剧大部分是围读以后就舞台见了,但这次,我们抱着很大决心,希望让演员真正沉浸其中。”
工作坊里,演员们围读剧本、彩排关键戏份、听音乐定调,再根据现场反馈调整剧本和音乐,确保每个人的唱段都与自身风格相得益彰。“这种做法费时费钱,但它才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高世章说。

·《大状王》剧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供图 )
2019年,《大状王》在香港预演,团队收集大量观众意见并进行修改,计划2020年正式上演。然而,受全球疫情影响,首演计划一拖再拖。“演员都已定下,大家都做好准备上台了,不能因为演出取消让他们没了工作。”高世章说,“所以我们拿演出预算,先录制了原声带,然后又录制MV,当时就一个想法,不能让这个剧的创作停下来。”
2021年,由刘守正、郑君炽主唱的MV《一念一宇宙》上线,一镜到底的后台全呈现引发关注。一年后,《大状王》终于在香港首演,一举成名。高世章仍记得首演当天的心境:“真的很紧张,整个话剧团在后台、场外等待,听到第一声鼓敲响,所有人都在喝彩——我们终于‘开幕’了!”

粤语很适合做成音乐剧
高世章出生于文艺世家,外祖父白玉堂在粤剧圈声名显赫,母亲尤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坛巨星,蝉联两届“亚太影后”,大伯母葛兰则是大名鼎鼎的“曼波女郎”。
生在这样的家庭,做音乐自然成为高世章的终极理想。“但家人从不鼓励我、支持我做音乐。因为他们很成功,知道成功的代价是什么,更知道时运的重要性。我也不知道命运会不会眷顾自己。”

·高世章母亲,两届“亚太影后”尤敏。
高中毕业后,高世章还是决定拼一次,前往美国西北大学追寻音乐梦。父母与他定下“一年之约”:“学音乐可以,但是不能只学音乐。我说给我一年时间读各个专业课程,如果最后还是喜欢音乐,那就是真爱。”
那一年,高世章从计算机课程学到宗教学,从哲学系课堂跳到经济系,“能想到的东西我都读了”。一年后,他还是一头扎进了音乐专业。“我以为父母会骂我,但都没有,只是说:既然选择了,就要做下去,没有回头路。”
大学时代,高世章每天都在研究、创作音乐,成绩名列前茅。毕业时,他得到在芝加哥合唱团当指挥的机会。“但我又想,做指挥太束缚了。导师跟我说,趁着年轻去纽约看看,纽约不等人。”于是,高世章向东海岸进发,考入纽约大学音乐剧专业。

· 《大状王》作曲、音乐总监高世章。
选择音乐剧,源于一场普通演出。在那之前,高世章也看过《歌剧魅影》 《悲惨世界》等经典之作,“就是想象中最好的音乐剧”。一次,他偶然看到学生排的《理发师陶德》,被剧中音乐深深震撼。大师桑德海姆,用极优美的旋律和悲壮的声调,将一个恐怖主题演绎出史诗般的厚度和耐人寻味的批判色彩。“他完全用音乐撑起了那么复杂的的故事。”
从那时起,高世章陷入了音乐剧的魔力。2003年,刚刚回港的高世章担任音乐剧《四川好人》的音乐总监。该剧改编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剧作。创作中,高世章巧妙融入《康定情歌》,采用半戏曲的演唱方式,让一部德国戏剧改编的粤语音乐剧拥有了川味。
也是因为《四川好人》,高世章接到陈可辛邀请,为电影《如果·爱》制作配乐,一首《十字街头》拿下多个大奖。
“《如果·爱》后,你们完全可以转向做收益更大的配乐工作,为什么始终坚持音乐剧?”
“我觉得人要不断问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想扬名立万还是自由自在?我的目的是发掘没人做过的东西,去年我在香港和日本举办一个融合戏剧、音乐、视觉艺术和气味的展览《琉璃之歌》,没人做过,因此极度满足。电影、配乐、流行曲,很多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音乐剧还没有人做得最好,还有很多空间。”
《四川好人》后,高世章、岑伟宗又合作了《顶头槌》《一屋宝贝》《奋青乐与路》等热门作品,成为香港音乐剧领域的代表人物。
1972年,由顾嘉辉作曲、黄霑作词的《白娘娘》,成为在香港上演的第一部华语音乐剧;1997年,《雪狼湖》破天荒将舞台搬至大型体育馆,创下“明星音乐剧”的巅峰。香港音乐剧发展半世纪,曾一度引领亚洲市场。
然而《雪狼湖》后,香港音乐剧许久未见“爆款”,“甚至其他地方都已经追过了香港”。在高世章看来,粤语音乐剧不该仅限于此:“以前总有人说,讲粤语的人太少了,但看看近些年韩国音乐产业的发展,几十年来国内观众对法语、德语音乐剧的热情,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借口。粤语原本的九音使其语言具有天然的音乐性,说话就像唱歌一样,是很适合制作音乐剧的。”
因此,《大状王》的成功大大增强了高世章的信心。8年前,他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推出《顶头槌》,开场只有一半观众;如今,《大状王》在同个剧场连演10天,天天爆满。
这就是他一直追求的“戏抬人”——戏好了,观众自然就来了。
 责任编辑:高玮怡
责任编辑:高玮怡高世章
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要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