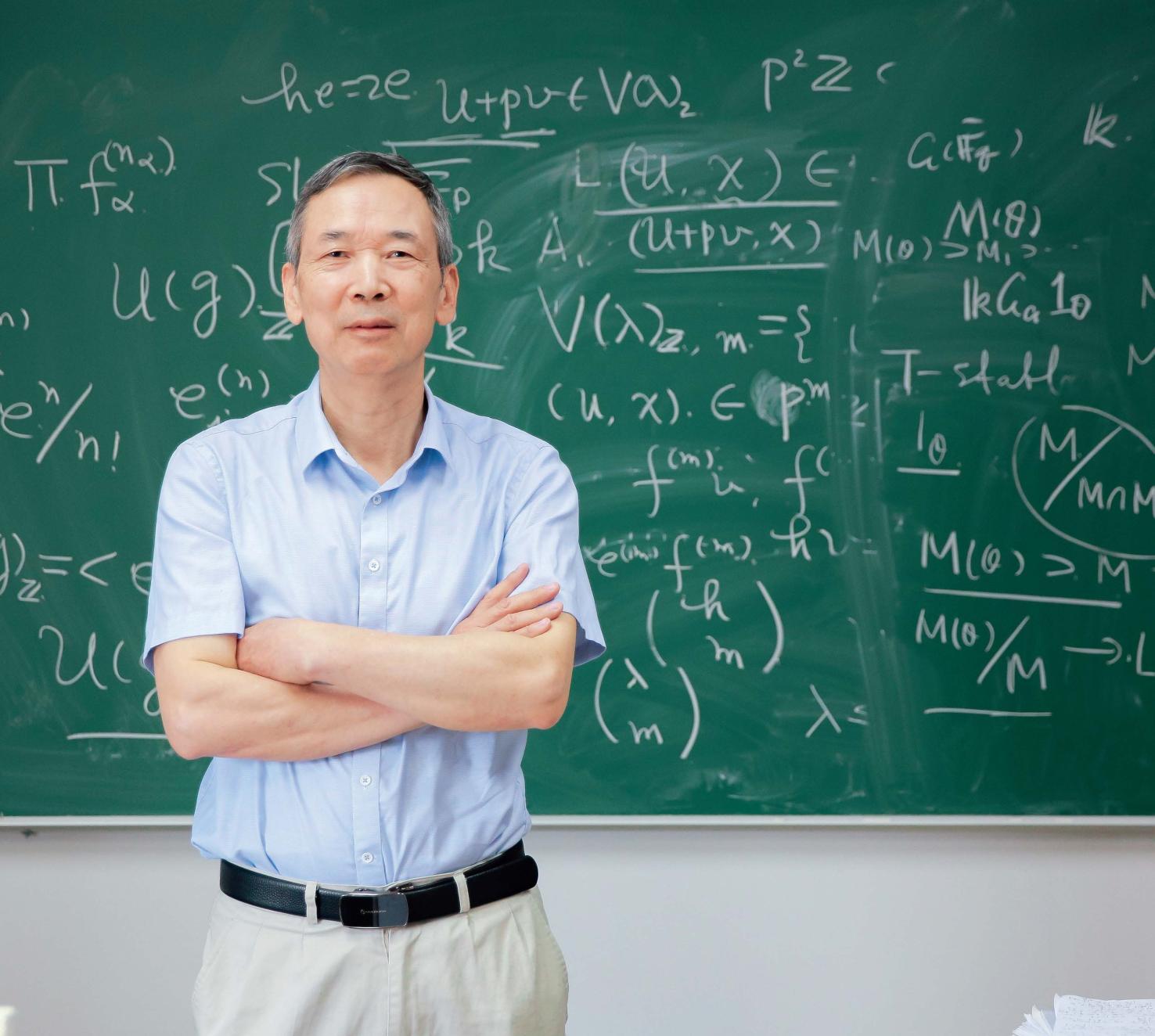
2025年6月5日,席南华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席南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1963年生于广东。2001年获晨兴数学银奖,2005年获中国数学会陈省身数学奖,200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曾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这恐怕是一次错误的采访。”一见面,席南华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自己是个“平庸的人”,多年来所做的也只是在试图理解数学。
这当然是自谦——他是我国知名数学家,从大专生一路逆袭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数学研究领域和教书育人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可席南华总觉得,和那些伟大的数学家相比,自己做的没什么了不起,“也就这个样儿”。
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松弛感。拍照时,记者请他多笑笑,他说这不太容易,然后一本正经地讲笑话,反逗得记者笑弯腰。聊科研,问他会不会因为一个难题研究多年却没有答案而失落,他坦然道:“知道自己做不出来,也是一种收获。”他从不内耗,哪怕是2005年做了肝移植手术后一度化验指标不理想,内心依旧平静。“那是医生要解决的问题,我不操心。”
用最直接的逻辑追寻最简单的答案,席南华的思维很“数学”。这使他做人简单,做事也纯粹。他说:“我觉得人越简单就走得越远,你只需要简单地朝着你的目标走就行了。”
考63分进了数学专业
采访在6月5日进行,临近高考,席南华与《环球人物》记者聊起了他的求学经历。
1963年,席南华出生于广东韶关英德县(今清远英德市),10来岁时举家搬到湖南。“当年,少年班宣传得非常厉害。我看到报道有点忧虑,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神童,我将来会是怎么个活法?”让他没想到的是,1978年,父亲鼓励正读高一的席南华提前参加了高考,目标是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脾气很糟糕。当时我们家有7口人,奶奶、父亲、母亲、我以及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养家的压力比较大,每当事情不如他意的时候,就会很暴躁。但对子女的成长,他还是很关心的。”席南华回忆道。
那场关键的考试,席南华考得不太理想,数学只考了63分,化学倒是考了80分,但他填写的志愿都是数学专业。与少年班无缘,席南华最终被湖南黔阳师范专科学校(后更名为怀化师范专科学校,现为怀化学院)录取,学的是数学。对此,父亲没生气——他对儿子的最高期望不过是“把字练好,以后给领导当个秘书”。但15岁的席南华感到沮丧,之后失利的阴云更是挥之不去:毕业前参加考研,他名落孙山,被分配到一个偏远中学教数学。
那时,学校所在的乡村还没有陆地公共交通,当地人靠水路才能到外面去。课余时间,席南华的消遣只有去附近的山上散步。有一回,他在山间小路上偶遇一头水牛,“四目相对,我觉得我不是它的对手,赶快给它让路”。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了。
1982年,席南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同学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我却连个本科学历都没有。他们的见识比我多,各方面都比我优秀,我感觉自己事事不如人。”读到第三年,论文还写得磕磕绊绊,席南华迷茫了,问导师曹锡华,自己是不是该回湖南找个工作。曹锡华问他:“你想不想念博士?”
“想啊!”席南华并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数学世界。“那你就继续读博士吧!”曹锡华鼓励道。
席南华就这样考了博士。当时正值市场经济大潮澎湃,许多人下海从商。同宿舍的同学劝席南华转行做经济工作,这样未来能发挥所长,收入也会多得多。但席南华不为所动:“纯数学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别的好像不太对我的胃口。”在他眼中,数学的世界至美、安宁,能给人带来快乐。
博士毕业后,他在数学领域深耕数十年,取得很多成绩,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其实没想过自己能为数学作出重大贡献,至今觉得自己很平庸。这种心态唯一的好处是我会因此不断努力,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思考哪个地方没做好。”席南华笑言,他的故事至少证明,一个平庸的人经过努力也能成为别人眼中优秀的人。

席南华(左一)参加大学生数学夏令营。
研究成果是“高度非凡的”
“数学家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这是席南华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搞数学研究相对自由,不用实验设备,走路、吃饭时都可以想数学问题,还可以去世界各地与同行交流,很快乐。他不喜欢外界将数学家片面地描述成“苦行僧”。“任何职业都有艰苦的一面,数学家并不比其他职业苦,至少我在全世界所见的数学家都很快乐。如果一件事情让你一点都不快乐的话,你也不会有动力和热情去把事情做好。”
谈及影响了几代人的数学家陈景润、近两年备受关注的北大数学老师韦东奕,席南华认为,大众对他们的认识常常是失真的,就好像站在很远的地方看风景,很多东西其实看不清,却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填补空白。“每个人都是多面的,数学家也不例外。”
席南华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起他不那么“高大上”的一面。1988年,他要从上海去北京,前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开启博士后研究。当时的火车票很紧张,他只买到一张别人的退票,赶在7月14日出发。“我一定要赶在7月15日报到,因为这样可以拿一个月工资。如果再晚一天报到,我就只能拿半个月工资了。”年轻时,席南华爱算经济账。
一年半后,数学所提出让他留所工作。他的第一反应是问:“我做博士后每个月有100元津贴,如果留所还有吗?”对方说没有了。他一想,自己还能做6个月博士后,答应留所就要损失600元钱,于是说不留了。对方想了想,又问:“那把钱补给你行不行?”席南华这下答应了。多年后回看,他评价当时的自己“眼光短浅”。
如果将时间线拉到1994年之后,人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席南华。从那一年到2005年,10余年间,他只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即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因为他嫌写申请书和后续报告太麻烦,浪费时间,影响心境,干扰研究工作。他一心扑在自己感兴趣的代数群与量子群研究中,从不为名利做任何自己内心不认同的事。当时,连许多数学界的同行也不了解他在干什么。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2005年,席南华获得中国数学会陈省身数学奖;两年后,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的研究成果还受到国际关注,一篇论文被美国数学会以单行本形式发表,被认为是“高度非凡的”;另一项研究成果在数学界四大顶级期刊之一的《美国数学会杂志》发表,这是大陆学者首次独立在该刊发表论文。采访中,对于这些荣誉,席南华反而说得不多。“得奖的话,我可能就是当时高兴几天。但如果做出了原创性的东西,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一直高兴。要是漂亮的成果被同行夸奖了,那更好;同行不夸奖也没关系,我可以自娱自乐。”
让数学更接地气
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数学组组长、“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学和应用研究”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席南华的头衔不少,社会工作也特别多,但最重视的还是人才培养。

席南华为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
今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他去重庆参加一场研讨会。平日,他会婉拒类似的活动邀约,但得知这场研讨会是关于中小学数学新教材的,便专门去作报告。他重视教材,“课堂之外,教材就是学生接触最多的资源”。
去年下半年,席南华在上海科技大学教线性代数,每周从北京去一趟上海,只为给学生们上课。一学期下来,他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缺乏好的理工科线性代数教材。他决定自己编写一本教材。他将上课时用的讲义整理好,按照听过课的老师和学生的意见进行修改后,交给了出版社。他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透露,这本教材很快就要出版了。
席南华也思考着如何让更多人对数学感兴趣。“每年诺贝尔奖的得主做了什么工作,大家通过媒体大概能知道。但是拿了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人到底研究出了什么,很少有人了解。数学就是很抽象、很难向大众描述清楚的。”他写起了关于数学的科普文章,还邀请同事一起写,却发现很多人欠缺写作能力,“写出来的文章给人板着脸说教的感觉,故事性、趣味性都不够”。比如有一篇的题目是《P值检验》,他觉得这个题目谁都没兴趣看,就将其改成了《真的吗?如何检验?》,更接地气。
在上课或讲座时,席南华会时不时穿插一些妙趣横生的小故事。“传说,法国天才数学家伽罗瓦(群论的创立者)21岁时为情所困,与人决斗,最终送了小命。我劝大家遇到感情纠纷还是要冷静一点,不然我们的数学事业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台下学生笑声一片。
生活中,席南华有着数学家的幽默与浪漫。他对妻子的昵称是“乖”,在澳大利亚访问时,看到妻子喜欢的栀子花,便摘下几片花瓣塞到信封里,寄回国送给她。“我爱人非常优秀、聪明、能干,把家里照顾得很好,工作也做得很好。我就很普通了,没什么独到之处。”工作之余,他喜欢看书,小说、历史、哲学,什么都看;为了健康,他也常去运动,游泳、散步、打球——采访前一天晚上,他还去打了两小时网球。
“我并不要求学生未来一定要从事科研工作,只要他选择的生活适合他,我觉得就挺好。”席南华快乐地工作、生活,也希望学生们有快乐的人生。“每个人的春天到来的时间不同。学习应当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关注的是自己的成长,而不是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别人的优秀与成功不是你头顶上的乌云,不会妨碍你的优秀与成功。眼下一时的高低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成长,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是席南华对学子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邱小宸
责任编辑:邱小宸席南华,数学家
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要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