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马伯庸,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茅盾新人奖得主。其作品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代表作有《食南之徒》《太白金星有点烦》《长安的荔枝》《大医》等。新近出版小说《桃花源没事儿》。
2022年秋天开始,马伯庸一口气出了3部书:《大医·破晓篇》和《大医·日出篇》,加起来80万字;《长安的荔枝》7万字;《太白金星有点烦》13万字。粉丝都“埋怨”他:你写得比我看得还快!马伯庸无奈地一摊手,“我其实写了4年多,只是机缘巧合,出版赶到一块了”。
后面两部小说,书脊上都有个红色的小印章,上面写着“见微”二字,意思是“见微知著”。那段时间新书发布,马伯庸总说,希望这个系列可以继续写下去。如今,《太白金星有点烦》舞台剧已经演过一轮;《长安的荔枝》话剧也正在巡演,电视剧版刚刚热播完结,电影版待映,马伯庸又“上新”了——“见微”第三部作品《桃花源没事儿》6月出版,18.7万字。
见到马伯庸那天,他穿着一款蓝色条纹短袖T恤,上面印着:“我每天努力工作”,旁边还有个小人,正拿着铁锹在坑边埋头苦干。看得出来,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从片儿警故事到奇幻小说
《桃花源没事儿》体量不大,却是一个陆陆续续填了12年的“坑”。
2013年,马伯庸成了新手爸爸。生活被工作和育儿塞满的他,唯一的喘息时间是深夜在楼下溜达时听片儿警朋友讲社区里的鸡毛蒜皮:邻里纠纷、夫妻拌嘴、猫狗丢失……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琐碎日常,悄悄在他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当时特别想写一个片儿警的故事。”马伯庸对记者说。他刚开了个头便搁置了,未曾想这粒种子在12年间不断变形——从现实主义的社区民警,一路生长为架空世界里的俗务道人,最终幻化成奇幻小说《桃花源没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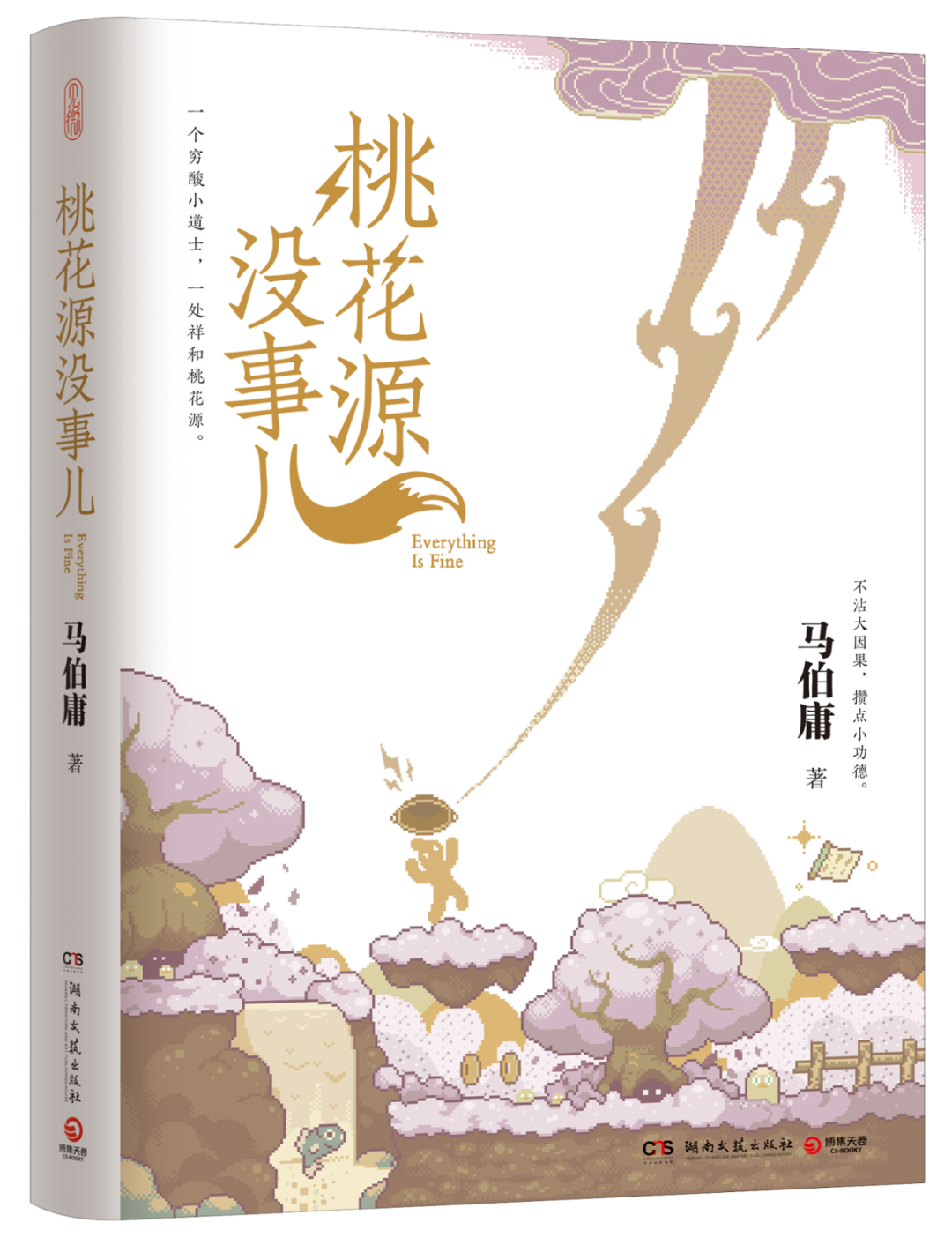
如果说同为神话志怪题材,《太白金星有点烦》还是对《西游记》的另类解构,把满天神佛都“凡人化”;《桃花源没事儿》就是把《桃花源记》里的地理、历史和《聊斋志异》里的精怪,以及《西游记》《白蛇传》等各种妖魔仙鬼“一锅烩”——蒲松龄笔下的婴宁与辛十四娘,《西游记》里的奔波儿灞,《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甚至民间传说中的蝙蝠精、龙王三太子、怪兽穷奇……都被烩进了马伯庸的“桃花源”。
这个“桃花源”,虽是修仙之境,却比人间还要充满烟火气。主人公玄穹是负责管理桃花源一众妖怪的俗务道士,命格清奇,一辈子注定发不了财,守着一份无望的工作,想卷没动力,想躺又觉得对不起自己良心。众妖怪的日常生活都是人间事:咬牙买下学区房的蜘蛛精、为儿子挣药费炼丹到秃头的狼精、书院里打架惹事的小精怪们……
汪曾祺当年写《聊斋新义》,说自己是“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马伯庸的《桃花源没事儿》,则是披着《聊斋》等各种妖怪的“皮”,根骨却长在锐利的现实里。
人物设定全凭作者喜欢。《聊斋》众多狐妖中,马伯庸最爱婴宁,只因她“让人特想交朋友”;辛十四娘则承载了他对原著人物命运的某种不甘——“既然聊斋我们改变不了,何不在另一个故事里,给她一次新的体验?”在马伯庸笔下,婴宁不再仅是烂漫娇憨的少女,她能力高超,但又总是纠结、自我怀疑,“就像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在职场冲锋陷阵,内心却常陷于困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胜任一个更好的职位”。 马伯庸把对她们的观察、倾听甚至劝慰,都化成了小说中婴宁的血肉。
当被问及是否会告知朋友们成了书中角色,马伯庸狡黠一笑:“底不能漏。送她们书,让她们自己悟去。”如同他笔下那个能看破一切幻象的主角名字——玄穹,“他悟不如自悟”。
书名“桃花源没事儿”也暗藏机锋。马伯庸点破:“人什么时候会说‘没事儿’?是真受伤了、真有事的时候。”骑自行车摔倒了,旁人来扶,你咬牙站起来说“没事儿”;项目搞砸被老板痛批,回家面对父母关切的眼神,你强笑说“没事儿”——“没事儿”是平凡人的生存铠甲,内里包裹着不愿示人的创口与坚持。

喜欢“具体做事情的人”
玄穹,这个被马伯庸调侃“记他的名字,记得穷就行了”的角色,实则是他“见微”系列的关键一环。
从《太白金星有点烦》到《长安的荔枝》再到《桃花源没事儿》,马伯庸笔下的“职场人设”层级一路下沉——太白金星李长庚位列仙班,天庭中高层,放在当今社会,至少算得上大厂里分管重要项目的高管;《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乃技术骨干,被上司陷害,分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算是又累又受气的中层;《桃花源没事儿》里的玄穹,彻底沦为“光杆司令”,成了一线基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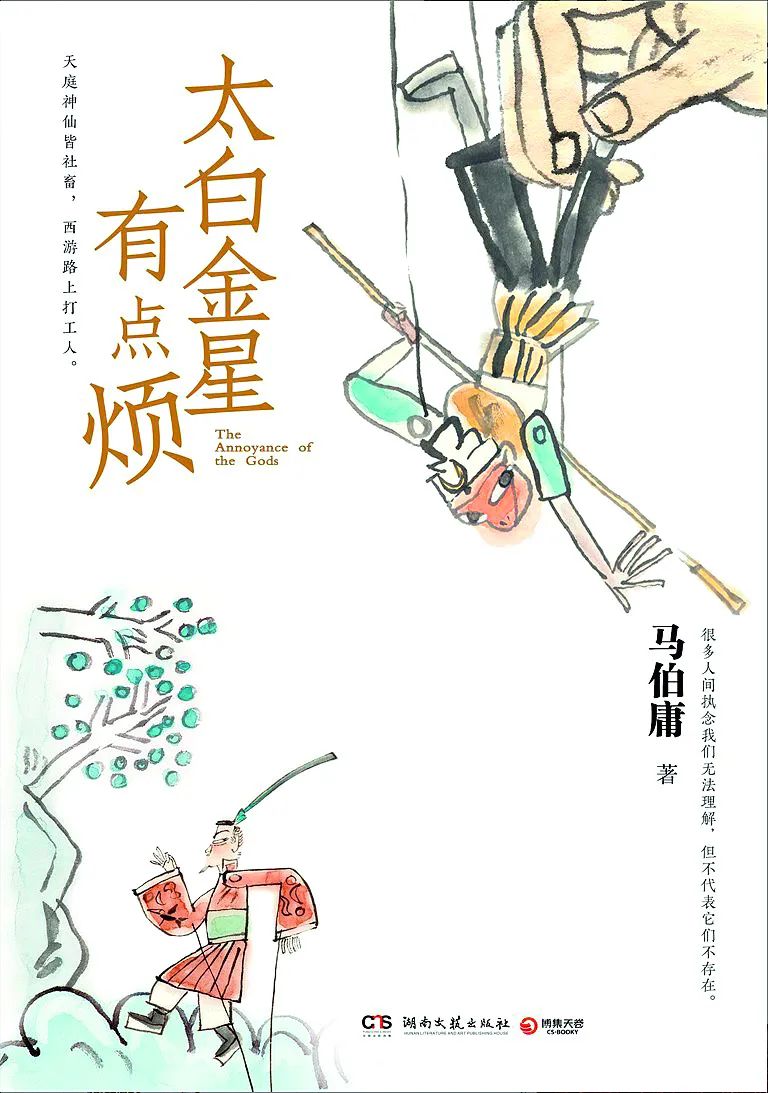
· 《太白金星有点烦》
“职场也分层次,”马伯庸解释,“每个层次状态不同,我想把他们一一写透。”
当读者为《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计算荔枝转运路线揪心时,马伯庸已经在他多年的写作中完成了一场历史书写的“视角革命”:“小人物比大人物更难。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更多时候是一事功成万头秃。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千千万万被史书省略的小人物。”与其说马伯庸喜欢写“社畜”,不如说他是喜欢“具体做事情的人”。
早期《风起陇西》聚焦三国谍战,《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刻画徽州丝绢税案里的讼状,近年《大医》将医疗史嵌入革命叙事,《食南之徒》则以“美食人类学”重构边疆史,马伯庸的大部头历史著作,也早就略过了帝王将相,总是在历史褶皱中寻找那些粗粝的生存真相。
“历史的魅力不在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而在青铜器上的一道划痕、竹简里记录的一颗枣核,以及被史书遗忘的姓名。”

《桃花源没事儿》写了12年,光阴浸润书稿,也留着马伯庸自己的岁月年轮。早期文字飞扬跳脱,玄穹与婴宁插科打诨的对话,满是当年混迹网络论坛的“中二”气息。写着写着,中年况味悄然渗入。学区房的焦虑、人生路径的迷茫,甚至反派角色的困顿,都成为书中无法回避的议题。“书里的人没老,剧情却开始老了,”马伯庸坦言,“做的事一件比一件沉重,一件比一件现实。”
玄穹挣扎在“挣不到钱、升不上去”的现实瓶颈里,满嘴抱怨,却在关键时刻死守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一旦突破,他就不再是他了。”这何尝不是马伯庸对当下无数“玄穹们”的寄语:当外部现实无法撼动,就在内心建一座桃花源。

“历史是墙上的一枚挂衣钉”
近年来,马伯庸一直保持着高产节奏,长篇间隙穿插《桃花源没事儿》这类“见微”小品,把写历史正剧的考据重负暂时卸下,任性地在架空世界撒个欢儿——“这是一种休息,一种任性,一种自我疗愈。”
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神怪题材,马伯庸都擅长在故事里注入令人痴迷的现场感。他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缝合虚实,用真实史实搭起故事的顶层,用生活细节铺满故事的底层。服饰、器具、书信、牌匾、建筑、家具……皆是他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虫洞。
他是一个细节狩猎者,素材积累已成本能。对唐代文化感兴趣,就关心唐代的考古报告,关心服饰、交通,吃喝拉撒的细节。11年没有目的性的积累,才能做到对素材了然于胸,11天写出一部《长安的荔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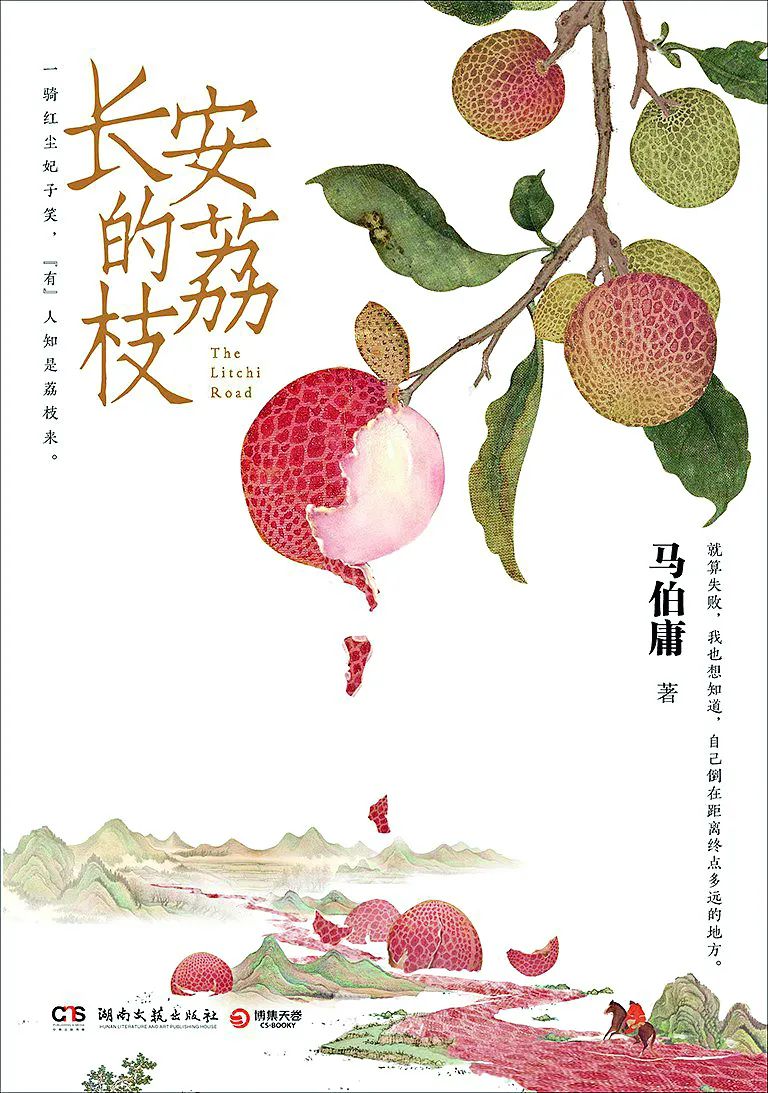
· 《长安的荔枝》
他喜欢漫无目的地闲聊,接触各行各业,打听趣闻轶事。一旦选定题材,便启动定向“深挖”,乐此不彼。
马伯庸清醒地知道,读者读历史小说读的并不是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跟自己产生共鸣的点。“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点,找到它的现实意义,这个小说才有价值。”马伯庸说。就像大仲马说“历史是墙上的一枚挂衣钉,用来挂我的小说”。只是除了历史,马伯庸还多了一个挂衣钉——神怪。
生活中,马伯庸对周遭世界总保持着一种好奇心。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打开软件搜一搜附近的地名,检索当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尤其是民俗传说、奇谭轶事,都能激起他极大的兴趣。
有时候,他还会一本正经地“恶搞”。他和朋友曾煞有介事地虚构出一种“鳄齿羊”的生物,为它手绘牙齿结构、伪造历史记载。这件事的初衷本只是为了整蛊一个朋友,最终因为编得太真了,甚至收到了一个动物组织的来信,要他们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并愿意给他们拨款。吓得马伯庸赶快解释,不然“再往下就是诈骗了”。
这些年,马伯庸的作品屡屡被搬上银幕或舞台,颇受好评。当被问及改编是否会影响写作时,他回答说,自己就好比开饭馆的厨子,只管把菜做好。至于这菜食客是否喜欢,能否被端上更大筵席,皆是后话。而所有创作的源头活水,仍是“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写到开心为止”。

· 《太白金星有点烦》舞台剧剧照。
这份“开心”的根系深扎于历史沃土中。中国5000年文明史对他而言,是永不枯竭的素材之源。“随便舀一瓢水,都够写一辈子。”所以他没有什么灵感枯竭的担忧,相反电脑里有一堆没写完的“坑”。
关于自己,马伯庸一直有着明确的定位——一个有趣的历史小说作家。“求真”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小说家则负责在坚实的学术地基上,用合理想象搭建引人入胜的空中楼阁。对他而言,故事“好看”足矣。对读者而言,唐诗里的荔枝与太白金星的KPI,奇幻的桃花源与现实中的困顿,已在人性的幽微处悄然贯通。
本篇文章刊登于环球人物2025年第13期(总第544期),原标题为《马伯庸,把“桃花源”拽入人间》。
总 监 制:张 勉
编 审:王晶晶
编 辑:陈 娟
 责任编辑:李佩蔺
责任编辑:李佩蔺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