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前查看天气预报,精准预测的阴晴雨雪让我们能从容安排出行;越来越准确的地质灾害预警,为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一道防线;不用接触身体就能够监测数据的“黑科技”,守护了很多独居老人……这些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背后,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支撑,那就是雷达。
从1953年设立国内首个雷达专业开始,被称为“雷达技术摇篮”的北京理工大学,就把中国雷达的发展建立在了自立自强的根基之上。70年的发展中,我国已在全球雷达技术的版图里构建了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而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的雷达、信息处理专家毛二可从未离开。
看不见的力量
毛二可出生在北平,七七事变之后,3岁的他跟随父母南迁来到了重庆。在大哥的影响下,毛二可接触到电磁波理论,并被这“看不见的力量”吸引,迷上了无线电。两兄弟一起做出了一台收音机,他依旧记得在重庆听到延安声音的激动。
后来毛二可成为北理工雷达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并留校任教。在中国雷达事业起步阶段,年轻的他意识到材料科学将是突破技术封锁的关键密码,并开始留心阅读相关文献。终于在1972年,毛二可在一篇美国文献中发现了熔石英在无线电信号传输中应用的可能性。又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毛二可的团队终于在杂波中看到了清晰显现的微弱目标信号。1977年,他带着成果参加了湖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

王宁:到了演习现场的时候,您心里是有点担心,还是挺自信的?
毛二可:我可以跟你讲个故事,那个飞机从远处飞过来的时候,一边飞一边往下撒那种金属箔条,就是为了干扰我们雷达用的,我们在普通的雷达显示器上,根本就看不见飞机了,全是干扰信号。然后我们打开了动目标显示装置,一瞬间,雷达显示器的干扰信号就消失了,只有代表飞机的一个亮点在快速移动。
王宁:您当时的心情是不是也跟那飞机一样,已经飞起来了?
毛二可:那一定是很激动,又感觉很自豪。
弹弓打麻雀
毛二可带领团队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最终解决了雷达“看得清”的问题。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雷达面临更多的技术变革。“看得准”成为毛二可要解决的首要难题。在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毛二可却觉得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那时的中国雷达团队,不仅要承受海上的日光暴晒,要从惊涛骇浪中的13米靶船支架上取回数据,更要接受反复试验失败的打击。
经历了一系列“靶场”测试后,毛二可团队将试验重心转移回北理工校园。测试运动目标从校园飞驰的自行车变成摩托车,速度依旧不够快。于是毛二可想到了自己童年最爱的活动——弹弓打麻雀。大型弹弓,将直径3厘米的钢珠高速弹射向天际。这个质朴的“科研神器”,破解了动目标模拟的世界性难题,更以极低的成本为中国雷达装上了“火眼金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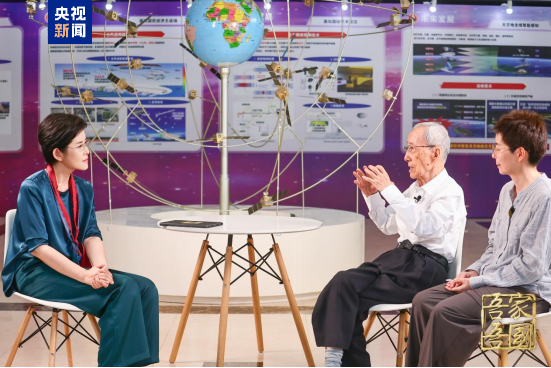
王宁:这么大的弹弓我真是没见过。
毛二可:一个高速度运动的目标,你要给它做出来,好像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成功。
王宁:那您做这个试验的过程也挺危险,万一要是打着人怎么办?
毛二可:我们都在没人的时候试验,所以节假日是最好的。整个学校都放假了,没人,我们就来大弹弓旁边集中试验。
王宁: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这样的一个简单装置,这么一个土办法,在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最高精端的雷达。
毛二可:别小瞧这不起眼的弹弓,有时候简单和复杂,其实只是一念之间,我就喜欢琢磨这些。
“科技—产业—科技”
中国成为继英美之后第三个成功研制出矢量脱靶量测量雷达的国家,毛二可的团队继续埋头科研之中。他们每年都会产生一大批科研文章,但几乎都在发表之后便被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了推进科技成果转化,75岁高龄的毛二可带领着北理工雷达研究所的十几位老师“下海”创业了。
毛二可团队成立的这家科学性企业在2013年实现了营收破亿,而他将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实验室,开启了“科技-产业-科技”的闭环模式。科研没有尽头,曾有一年春节,学校为了让毛二可回家休息将教学楼的电闸都拉掉。他就这样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他迷恋的雷达事业。

王宁:您喜欢的东西和您这辈子做的事,是一件事,这是最幸福的。
毛二可:对。
王宁:您对无线电,对雷达热爱的起源是从您中学开始的,是吧?
毛二可:是,刚开始我就是喜欢这个,到后来我一辈子就干了雷达这一件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为国家做点事,我很满足。你看现在咱们国家很多雷达技术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我没白干。
 责任编辑:高玮怡
责任编辑:高玮怡毛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