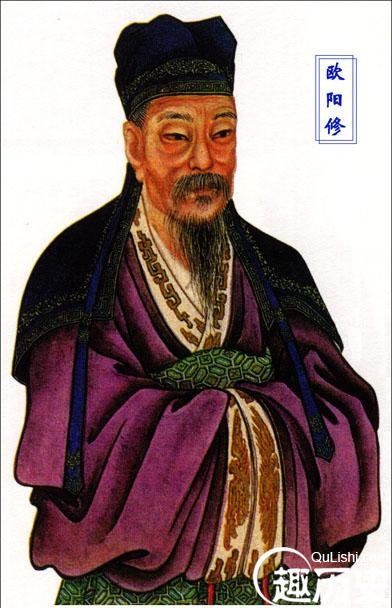
《醉翁亭记》的价值不止于文学,欧阳修撰写此文的心态与思想,也颇堪玩味。
志士何以成醉翁
《醉翁亭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的滁州,想要了解文章创作的心态,必先联系欧阳修的仕途起伏。
欧阳修自步入官场,稳中有升,亦是以范仲淹为首“改革派”的头面人物之一。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以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赋予欧阳修等谏官超过以往的权力,允许其上朝议政。然而,“庆历新政”历经一年有余便偃旗息鼓,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改革。
欧阳修从来都是与改革派共进退,改革失败的“标配”自然是相关人员的贬谪外任。反对派竟罗织欧阳修的私德“污点”来攻击他——欧阳修有一位外甥女张氏,年幼时丧父投靠,欧阳修将其许配给堂侄欧阳晟。谁承想张氏与男仆陈谏有染,私情被欧阳晟抓住,并投入官府。而审理此案的开封府尹杨日严,曾因贪污渎职遭到过欧阳修的弹劾,这次便抓住时机,诬蔑张氏在未嫁时,与欧阳修有不正当关系。这种“无稽之谈”在改革派失势的大背景下,俨然酿成一场风波。最终,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的欧阳修,被左迁至滁州(今安徽滁州)。
欧阳修自然无法容忍这种攻击,同时,他也知晓自己难逃贬谪的命运。于是他在《滁州谢上表》中说道:
盖荷圣明之主张,得免罗织之冤枉。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意在表明,自己充分领悟并感激宋仁宗的处理,但也再次控诉群奸宵小的诋毁。奋斗十载的理想夭折,心心念念的革新气象消亡,欧阳修成为“醉翁”,几乎不是因为贬官,而是他前半生的志向与事业,遭遇重大挫折,他内心的失落与愤懑,不言而喻。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仕途坎坷而纵情山水,在传统诗文中由来已久。《醉翁亭记》的第一处关键句是:
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首先,关于“醉翁”这一称呼,就比较矛盾,因为欧阳修并不嗜酒,年纪也仅有四十。那为何自称“醉翁”呢?他在《题滁州醉翁亭》曾写道:“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意在消除痛苦,而非颓丧饮酒——“酒”被视为削弱痛苦的媒介。
其次,酒与醉只是山水佳景的助兴之物,欧阳修的着眼点还是自然,与其说是沉醉美酒,不如说是沉醉于自然。只有这样,他才能观察并描写出琅琊山四季的美景。
写作《醉翁亭记》的同一年,欧阳修还创作了《丰乐亭记》,两篇文章堪称“姊妹”篇。《丰乐亭记》侧重于描述宋朝以来,滁州的河清海晏,大部分篇幅聚焦于历史,不过,此文最后,也有和《醉翁亭记》类似的表达:
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可见,这种悠游山水的心态时时相通。经历政治挫败的欧阳修,将“山水”作为舒缓情绪、寄寓心事的佳所。滁州固然是人杰地灵、风景如画,但更因欧阳修心态如是,方能将其妙处诉诸于文。
与民同乐的欧阳修
如果欧阳修仅仅纵情山水,《醉翁亭记》绝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山水寄情之外,“与民同乐”的观念,才使其文其人熠熠生辉。
欧阳修很早便形成并认同“与民同乐”的理念,并始终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宋史》曾记载:
(欧阳修)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夷陵积压的冤假错案,深深触动了欧阳修,当朝臣们言之凿凿地发表宏论时,县里百姓却很可能因为太守的玩忽职守而家破人亡。国家社稷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由黎民苍生组合而成。这应当是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超乎同辈的深刻认知。
《宋史》评价欧阳修“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也就是不求功名、只看实际,把百姓幸福当成执政的唯一目标。
如果我们把欧阳修的思想与“庆历新政”稍加联系,也不难看出一脉相承的思路。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提出十项主张,历来被视作新政的发端,十条改革建议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其中,“明黜陟”就是严格考核官员政绩,奖惩分明,全然针对吏治。“择长官”则是“明黜陟”的应用层面,即根据考核,谨慎任命官员。“抑侥幸”是企图削弱恩荫制度的作用,减少权贵子弟的入仕;“精贡举”则是重视科举取士,着重考核真才实学,而非纯粹的诗赋经义。
实际上,所谓“庆历新政”,真正有所动作的变更,侧重于前四项,目标便是解决冗员之弊,让各级官员能够真正履行责任,为社会造福。曾为范公鼓与呼的欧阳修,当然也认同这些主张。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结尾说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不是一句行文到此的场面话,而是欧阳修政治思想和爱民情怀的一抹动人“痕迹”。
 责任编辑:蔡晓慧
责任编辑:蔡晓慧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