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王澍,1963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建筑设计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硕士、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2012年成为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
要找到王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联系采访时,中国美术学院的宣传干部就不断提醒人民文娱记者:“一定要多打几次,王老师不爱接电话。”果不其然,一直没接。
不过,这样的事在王澍身上再正常不过了。2012年,他获得世界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奖后,无数人想找他做项目,大多铩羽而归。后来,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两名杭州富阳区的干部就在酒店电梯口“守株待兔”,这才“抓”住了王澍。这一抓,就抓出了文村——这座位于杭州富阳西部偏僻山区里的小村庄,如今已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

·文村一隅。
许多人用隐士来形容王澍。他有时隐于野,带着学生到山林去,到乡村去,“要找到活着的中国文化只能到乡村去”;有时隐于市,在城市繁华处寻找旧韵,在工地上和工人们聊天、干活,“他们都特有智慧”。
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构筑了王澍对中国城乡的理解框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他的提案也总围绕城与乡:2023年,他聚焦中国城乡实体文化记忆的保护问题;2024年,他关注城乡更新配套政策和乡镇文物保护修复;今年,他提出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城市肌理的保护是不可突破的底线。
记者终于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协小组会议上“抓”到了王澍,听他讲述自己的调研故事、提案内容,仿佛也看到了中国城乡建设的发展图卷。
城市更新,不搞大拆大建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令王澍印象深刻: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形成一批示范性合作成果。这句话出现在“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段落中。“小而美”3个字让王澍颇有感触:“在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地方习惯了大拆大建。可对老百姓的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小而美’。”
“小而美”意味着城乡建设不再一味追求数量,而更重视质量,重视文化,重视人性化和个性化。今年全国两会上,王澍聚焦“城市更新”的议题,其落点和“小而美”的提法不谋而合。
城市更新是近些年备受关注的话题: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中心地区不可避免会面临人口减少、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这些地区的更新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忽略的课题。
然而,如何有机、有意义地更新,如何从“开发性更替”向“适应性再生”转变,始终需要建设者不断摸索、思考。在王澍历年的调研中,遇到过不少令人心痛的案例:在某历史街区,当地的更新做法是把旧砖切开,把所有房子重新“贴”了一遍,“这简直是在毁坏,打着保护、棚户区与危房改造、文旅开发的名义进行的破坏性开发到处可见”。
粗暴型的更新不仅带来了破坏,还造成了“千城一面”的现象,最终使得城市的底蕴不断被消磨,文化特征渐行渐远。“这样会让我们的城市变成没有回忆的城市——一座城市没有回忆,就像一个人的生活没有回忆一样,是非常可怕的。”王澍对记者说。
因此,王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城市肌理的保护是不可突破的底线。以他主持的杭州中山路更新项目为例。2007年,杭州市政府找到王澍,希望他主持中山路南宋御街历史街区的综合保护与更新。这里曾是杭州最繁盛的街道,聚集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建筑,却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向破败。更新方案讨论了6年迟迟不能落地,几经辗转,项目落到了王澍手里。

·杭州中山路。
就这样,王澍带着中国美院200多名师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调研,细致到连一个具体的门牌号都要记下。最终,他拿出了全新方案:停止拆迁,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木构民居、民国建筑和近50年的砖混民居。在他看来,本地居民也是维系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向市政府汇报时,他特意写了一句话:“不搞大拆大建也可以做。”
经过3年改造,一条小巷密集、建筑各异的新街区完成了。没有宽大的马路,也没有林立的高楼,却在开放一周内迎来了100万市民参观,至今仍是杭州地标。“这种改造在中国可以发生,说明我们有机会和优势在文化保护上走出一条与外国不一样的路径。通过有机更新,可以做一些让城市更有生命力的事。”王澍说。

·杭州中山路。
到乡村去
2023年,王澍的名字常和两件事绑定。第一件,是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城乡实体文化记忆保护问题的提案;第二件,是电视剧《三体》热播,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作为剧中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成了网红打卡地。
 ·电视剧《三体》中,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成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取景地。
·电视剧《三体》中,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成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取景地。
两件事看似无关,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直以来,乡村调研是王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也始终相信:“要找到活着的中国文化就要到乡村去。”他对乡村、对老房子,天然有一种亲近感。曾有人问他“什么是好的建筑”,他答:“对我来说,几乎中国所有的传统建筑都是好的建筑,我在任何马路边上看到的一个老农舍都是非常好的……在那个地方,你能看到一种真正平静的、美好的生活状态,它很真实。”
他也在乡村汲取了许多灵感,比如他曾在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宁波即将绝迹的“瓦爿墙”。沿海多台风,墙体被刮倒后,老百姓就会把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砖头、石子、瓦片混在一起重新堆砌成墙,4平方米的墙里能数出80多种不同的材料。2005年,在设计宁波博物馆时,王澍就将瓦爿墙和混凝土墙结合,打造出高达24米的现代瓦爿墙。
 ·宁波博物馆瓦爿墙和竹模混凝土。
·宁波博物馆瓦爿墙和竹模混凝土。
宁波博物馆开馆后,有一位宁波本地老人半年来了4次,每次来也不参观,只是不断用手触摸着外墙。他对王澍说:“这面墙就是我家的墙。”后来,王澍几次与人谈起这件事,越发意识到留存文化记忆的重要性:“我们迫切需要严格立法来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不能让中国城市与乡村变成没有记忆的地方。”
在王澍看来,这份文化记忆绝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复刻,或者简单地保护,而是要真正把人与建筑、传统与现代连结起来。2012年获奖后,在电梯口堵王澍的两位富阳干部,一开始是希望他为当地设计一个博物馆。然而,王澍在调研中发现,全区299个村子,保留原始面貌的仅剩1/10左右。于是,他争取了一个新项目:“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做(改造)一个村子,我就不给你们设计这个博物馆。”
4年后,14栋、24户农居“生长”出来: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的外立面,全部是就地取材,与明清老建筑相映成趣。在房屋内部,院子、堂屋甚至柴火灶台也被保留。
这14栋建筑,让文村一夜成名。一些年轻人返乡开设民宿,文村的年客流量达到10万人。
 ·文村景色。
·文村景色。
在改造过程中,王澍坚持为每一栋农居留下小院子。“中国人的传统生活,结婚、生育甚至死亡时举办典礼,都和院子有关。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院子,也会给生活带来变化。”小小的一块地,留住的是中国人的“院落记忆”。
在王澍眼中,建筑的时间性有时比空间性更重要。这个时间,可以是一代人的生活痕迹,像文村的小院,宁波博物馆的瓦爿墙;也可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脉络,像他从《山庄图》《溪山清远图》等宋画中勾勒出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轮廓,把龙泉青瓷的梅子青融进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青瓷屏扇中。
 ·杭州国家版本馆主书房南檐廊。
·杭州国家版本馆主书房南檐廊。
建材是冰冷的,建筑却可以是有温度的,因为它承载生活、承载记忆、承载历史。
建筑是为生活而做
在业界,王澍被誉为“中国最具有人文气质的建筑家”。
他建筑系出身,上世纪80年代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读书,从本科到硕士。90年代初,商品化浪潮来袭,中国建筑进入热火朝天的时代,他则选择隐居,开始了在西湖边钓鱼喝茶的生活。后来,他到同济大学读建筑系博士,2000年毕业后到中国美术学院任教,直到现在。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筑艺术学院。
其间,王澍一边教书,一边做建筑设计,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宁波博物馆、富春山馆等都出自他之手。这些年,他用中国山水画、园林艺术和传统工艺,慢慢形成自己的建筑语言,表达着中国现代建筑的方向。
“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建筑。”王澍说。在他看来,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的人文气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朴素建构艺术中光辉灿烂的语言规范和思想。
人民文娱: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工智能的话题一直很热。您如何看AI在建筑上的运用?
王澍: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AI的最强大处在于它是一个“超级复制机器”,是一个以复制为基础,之后再进行学习、改编的技术。其实现在中国建筑界大部分的操作模式就是“AI式”的,模仿其他的建筑,快速地进行改编,只不过AI可能会加速改编的过程。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效率的提高和创造力的提升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建筑现在更缺乏的不是效率,而是原创性的创造能力。
人民文娱:所以,您在对学生的教育上也非常注重多元化的形式,像乡土教育这种形式,几乎贯穿了他们整个学习生涯。
王澍:建筑是为生活而做的。如果一直复制前人之作,建筑就会变得非常狭隘。所以,我要让学生理解生活是怎么发生的,生活是怎样变得有意思的,需要用不同的途径:到乡村去采风、调研,教教他们拍小电影、做戏剧,或者写小说……
西方基本的建筑教育是抽象的、雕塑般的审美,但中国的建筑传统从来都是融化在环境和生活中的,这两种文化背景区别很大。但是我们的建筑教育基本上非常西方化,这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一种真正和中国文化有关的新的建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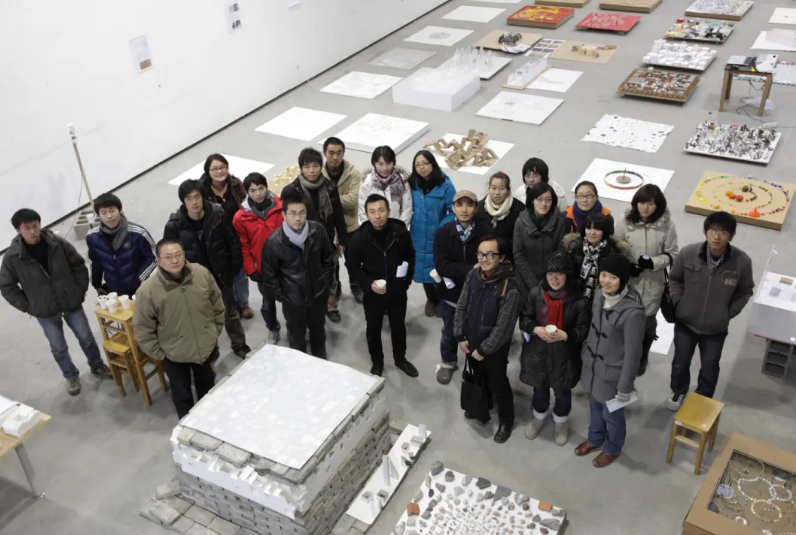
·王澍在课堂上。
人民文娱:您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一段事业上所谓的“空白期”,那恰恰使自己有了可以深入生活的机会吧?
王澍:的确,我基本上停下不做设计了,“混”在市井之中。我们在大学里学完之后,对生活是不了解的,实际上是把自己封闭进了一个与普通生活隔绝的空间。回不到生活你就回不到中国,回不到中国文化。包括在工地上和工人们接触,你会发现中国人真正的智慧,比如说一堵墙,用混凝土浇坏了,他们就非常巧妙地凿墙,凿完之后像壁画一样的美,他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创造了艺术。后来,我就把这种做法运用到自己的设计里。
我们的乡土中有一整套很有艺术含量的东西,几千年都存在。这需要中国建筑师不断去发掘。
 ·杭州国家版本馆俯瞰。
·杭州国家版本馆俯瞰。
人民文娱:现在回想那段空白期,最大收获是什么?
王澍:我觉得真正能够做出原创性事情的人,几乎都有空白期。他必须和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流拉开足够的距离,对世界有陌生感,之后开始产生新的想法。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己追求的氛围中,才是原创性发生的基础。
 ·雪中的中国美术学院。
·雪中的中国美术学院。
人民文娱:对于中国现在的年轻建筑师,您有何寄语?
王澍:不要简单地沉迷于科技的浪潮,科技当然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越是重要的时刻,越要回归人性。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余驰疆
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要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