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画片《大闹天宫》海报。
引爆关注的,为何又是“悟空”?
回首数一数,1961年,他是“国产动画之光”里勇猛矫健的少年;1986年,他是电视荧屏上有情有义的行者;1995年,他带着无厘头的戏谑闯入无数人的影像青春;2000年,他在网络小说中成为传主,反抗天地秩序;2015年,他是动画大片里的“中年大叔”,重燃人们对国产动画的希望;2024年,他是国产3A游戏里的灵魂人物,带领中外“天命人”降妖除魔。悟空已反复成为文化爆款,陪伴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
“我们一直强调文艺的时代精神,但孙悟空却从不过时,这是颇为神奇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惠元用将近20万字的著作《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三联书店,2024年再版)系统梳理了近一个世纪间孙悟空的形象变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发热潮之际,《环球人物》记者邀请他共同重温孙悟空的故事,并从“七十二变”的前世今生里,一窥现代中国的诸多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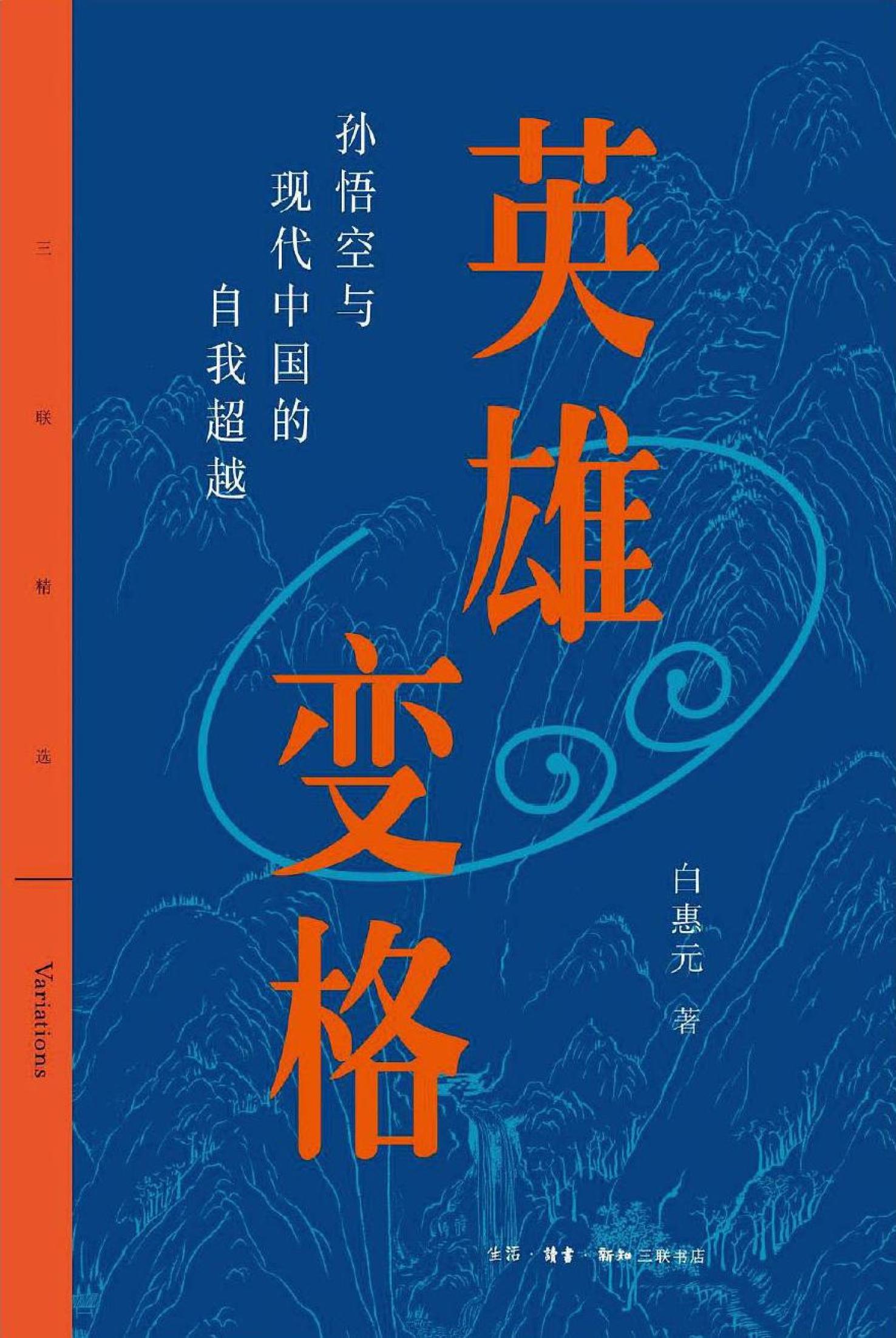
白惠元在书中系统梳理了近一个世纪间孙悟空的形象变迁。
60年代,“探民族风格之路”
1959年底,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大闹天宫》摄制组,严定宪担任原画组组长。时年23岁的他已参与过4部动画片的制作,包括“探民族风格之路,敲喜剧样式之门”的先驱之作《骄傲的将军》。
在严定宪接过孙悟空形象绘制的重任之前,同事们已经设计过3个版本,导演万籁鸣都不太满意。严定宪反复研读《西游记》原著,终于画出那版家喻户晓的孙悟空:他拥有接近真人的身形,穿着威风凛凛的黄色上衣、虎皮短裙、大红裤子和黑色长靴,兼具猴性、神性与人性。
孙悟空的脸则脱胎于京剧脸谱,一看就是来自中国。为了让孙悟空动起来,严定宪去请教被誉为“南猴王”的戏曲演员郑法祥,学习猴戏的经典动作,比如站立时要耸着肩、端着手、缩着脖子。
1961年,《大闹天宫》上集问世,好评如潮。严定宪生前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动画片本来就是舶来品,中国人应该怎么搞?我们不应该像美国人一样,单纯把这个当成一种娱乐趣味,一味搞笑,而是应当搞出艺术性,搞出意境。”
《环球人物》:作为中国动画史上的里程碑,《大闹天宫》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您对其中的哪些细节印象深刻?
白惠元:首先是造型上的民族化探索。20世纪40年代,万籁鸣导演了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孙悟空形象明显借鉴了迪士尼的“橡皮管”风格,头大身小,头身比例为1∶2左右,更像米老鼠。到了《大闹天宫》,孙悟空的造型更具民族特色,身体有所“发育”,线条更具弧线感,突出其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少年动态。
其次是影片的第一句台词:“孩儿们,操练起来!”随着孙悟空在花果山喊出这句话,画面转入猴子猴孙挥舞兵器组成的军事武装方阵,传达出“保家卫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这个开头为全片奠定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基调:“花果山”就是中国的隐喻。
《环球人物》:在影片中,面对天庭的招安,孙悟空却质问:“谁要他封?”您怎么看待这一情节设置?
白惠元:花果山对天庭的拒绝正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的心境表达和国际姿态——新中国被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国霸权,中国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之路。
《环球人物》:是否可以说,从《大闹天宫》开始,孙悟空这一神话里的英雄,有了更多现实的意义?
白惠元:是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力建构了孙悟空形象的反抗性。《大闹天宫》上下集采取相近的结尾定格镜头——孙悟空面带笑容仰望天空,周围环绕着高举手臂的群猴,那是专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庆典,是人民对新中国的自信与期许。
80年代,“敢问路在何方”
1981年,中央电视台委派导演杨洁筹拍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的造型怎么做?戏曲界的老艺术家认为,孙悟空还是要按戏剧舞台上的办法勾绘脸谱。但杨洁有不同想法,她认为“美猴王”就得美一点,于是前往北京电影制片厂(1999年并入中国电影集团),找到化装师王希钟。
王希钟与杨洁一拍即合。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他用上了绢纱粘双眼皮、硫化乳胶塑形等绝技。孙悟空的鼻子要像人,因为猴鼻子不太美观;嘴巴要像猴,突出“毛脸雷公嘴”的特点……1986年版《西游记》首播收视率达89.4%,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成为全球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其中的孙悟空,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

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火遍中国大江南北。
《环球人物》:“美猴王”成为86版孙悟空形象的代名词。在您看来,为什么“美猴王”之“美”不是单纯的审美范畴,而是一个社会化议题?
白惠元:“美猴王”之“美”,是导演杨洁进行艺术再创作的理念之一。这一版本在化装扮相上有了重大创新,彻底去掉戏曲脸谱,明确淡化舞台痕迹,追求更为生活化的表演方式。孙悟空的表情细节也就更接近于“人”,更易被审美化。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人道主义思潮兴起,中国社会掀起对于“美”及“美学”的空前关注。美猴王之“美”恰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感性氛围,折射出民众对于“新时期”英雄的想象方式。
《环球人物》:86版《西游记》的另一创新是走遍中国进行实景拍摄。这种实景构建了怎么的民族——国家想象?
白惠元:取景地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创作方式。如杨洁导演所言,名山大川、古典园林、佛刹道观都被摄入剧中,让“游”成为主线。这是一种“风景民族主义”策略。86版《西游记》通过电视剧里的4A、5A级景区,在“客厅”与公众、家庭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召唤出民众对祖国的文化认同。
《环球人物》:1986年秋季,电视剧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被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艺宣传材料。它何以成为时代的旋律?
白惠元:把《西游记》的故事主题解读为“寻路”,正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据词作者阎肃回忆,他先是写出了前半段,却感到缺乏深度,于是闭门细细思考。一旁的儿子说,他在地上走出了一条道。这才使他想起了鲁迅小说《故乡》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意境正好与取经故事相符,于是,他写出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结句。
这两句话可谓凝结了整部剧的核心精神,成为“摸着石头过河”在大众文化场域内的再现。所谓“路在脚下”,再一次确认了“中国”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在那个历史节点上,中国急切地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之路。
世纪之交,当古典遇上“网络一代”
1995年,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红遍内地。“我猜中了开头,可是猜不着这结局”“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等经典台词,至今仍以各种形式在网上流传。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结尾,夕阳武士收获了爱情,孙悟空则扛着金箍棒远去。
一名80后“星迷”这样写道:“《大话西游》看第一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看第二遍会大笑不止,看第三遍会泪流满面,看到第四遍时,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和无奈,可又说不出来。”
内地观众为《大话西游》赋予的丰富内涵,甚至超过了主创的预期。编剧、导演刘镇伟就曾坦言:“他们解读以后,(这部电影)才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电影。这个光环是他们扣在我的头上。”
《环球人物》:《大话西游》催生了一股蔚为壮观的“大话文化”,包括孙悟空在内,一切传统似乎都可以被颠覆。您怎么看这种颠覆?
白惠元:在此之前,孙悟空的形象一直都是很“重”的,被赋予很多意义;到了这里,他变得“轻”了起来。作为“准网络时代”的文艺作品,《大话西游》解构了各种崇高的表述,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孙悟空变成了至尊宝,是一个苟且偷生的山贼。
这种“反英雄”的、用戏谑对抗严肃的“大话文化”,可以视作“网络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它最初上映时反响平平,是大学生们在高校网络论坛上自发展开的“贴台词运动”让它彻底流行起来。从落魄的至尊宝到皈依的孙悟空,这种嬗变承载着90年代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心事。
《环球人物》:《大话西游》之后,2000年开始连载的网络小说《悟空传》引发了新一轮的悟空热潮,被一代人奉为网络经典。您认为它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白惠元:《悟空传》这部小说将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归于青春叛逆,指出人终将走上“取经之路”,走向成熟,但也希望激励读者在无聊的取经路上重拾大闹天宫的激情。这种“成长”的世界观与“老男孩”式的自我激励,是《悟空传》与《西游记》的根本差异,也是当代中国青春文化的征候之一。
新世纪初期,复兴路上的自我期许
2014年的一个冬日,制片人路伟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信息,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众筹发行宣传经费。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右二)、江流儿(左一)和猪八戒(右一)。
当时,这部电影已进入了制作的第七个年头。它讲述的是不一样的西游故事:小和尚江流儿偶然救出了被压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他法力全无、手戴铁铐,只盼遁世、不敢梦想,但江流儿坚信他就是齐天大圣。
次年7月,《大圣归来》剧烈地搅动了中国大银幕。它不但刷爆社交媒体,还催生了一个新词“自来水”——因为喜爱,网友们自发成为电影的宣传者。
路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更希望《大圣归来》是一个符号:“让更多的人在动画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加轻松一点、开心一点,也更远一点。”
《环球人物》:《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少年感十足,但到了《大圣归来》,他成了一位“中年大叔”。您怎么看待这种演变?
白惠元:在原著《西游记》第三回中,孙悟空将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去,自此,他的生命便与时间无关了,是无法感知青春或衰老的。因此,将“年龄”与“时间”铭刻于孙悟空的身体形态,本就是一种现代性改写。
在《大闹天宫》等前作的基础上,《大圣归来》对孙悟空的艺术形象进行了再创作。孙悟空首次被置于“父亲”的位置,唐僧变成了儿童江流儿,师徒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
《环球人物》:“中年悟空”切中了怎样的时代精神?
白惠元:如果说《大闹天宫》的少年悟空体现了新中国的革命乐观主义,那么《大圣归来》的中年悟空则是中国在复兴路上的自我期许——从稳定应对世界金融海啸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迫切需要从主体性出发,在世界舞台上讲出自己的“故事”。中年悟空历尽沧桑,最终挣脱镣铐、恢复神力,重新成为英雄。他又一次触动时代众生的情绪,彰显着空前的民族自信。
《环球人物》:分析《大圣归来》时,您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术语——“二次元民族主义”。
白惠元:2015年,我误打误撞地走进电影院看了《大圣归来》。影片结束,我旁边的两名中学生泪流满面,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终于有希望了!”这句话在我的心中停留了很久。
《大圣归来》的票房成绩主要归功于国产动漫受众的重复消费,这种现象可称作“二次元民族主义”。粉丝通过重复观影行为彰显其民族认同感,进而抵御外来动画的市场占有。正是《大圣归来》的成功让国产动画创作者看到了希望,“国产动画宇宙”变得越来越有生命力。
2024年,“世界品质”与中国故事
截至2024年8月23日21点整,《黑神话:悟空》全平台销量超过1000万套,成为史上最快达到千万销量的单机游戏之一。
一个多小时后,制作人冯骥在微博发出这段文字:“在我的身后,是所有游科同事与合作伙伴不懈的努力,是各位玩家近乎盲目的信任与从未衰竭的鼓励,更是依托于祖国的繁荣、稳定、包容与远见。”
《环球人物》:您认为这版“天命人”悟空有哪些时代特征?
白惠元:其一,游戏开始时,主角有一种强烈的“配角感”,他只是花果山的无名小猴。这是现在很多文艺作品在强调的,“主角光环”不要太重。比如《中国奇谭》“小妖怪的夏天”这一集,孙悟空是大人物,观众代入的却是“打工人”小猪妖的视角。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配角时代”,年轻人普遍认为自己是生活的配角。

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天命人”视角。
其二,是“天命人”这个称呼。我认为“天命”意味着一种不可撼动的秩序,或者说更高维度的支配。目前游戏曝光了两种结局,一种是常规结局,“天命人”发现自己就是悟空,戴上金箍,成为大圣;另一种是隐藏结局,“天命人”拒绝了金箍,决定反抗到底。
这折射出当代青年的境遇:面对生活中的秩序或支配,怎么办?创作者其实给出了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
从游戏体验上看,玩家以悟空的视角踏上冒险之旅,去战斗、升级、由弱变强,这本身就是一种英雄的成长叙事。我注意到,游戏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一些主播24小时直播,在某一关卡上一遍遍地失败、重来、继续,只为走完全程。这也像一种现实隐喻:英雄意味着对抗虚无,在虚无中寻找意义。即使需要一次次的重复劳动,我们也仍然在期待那个崇高的时刻,期待某个瞬间的突破和升华。
《环球人物》:刚才说到“配角感”,游戏中的许多配角很出圈。
白惠元:《西游记》原著的一大魅力就是妖怪各有特性和真情,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我对游戏的突出感受是,它就像一个“妖怪故事集”,对各种小妖怪的故事进行了“打开”。
比如第一单元的广智和广谋,在原著中就是两个小人物,但游戏丰富了他们的故事,让配角有了说话的权利。玩家每一次战胜妖怪后,都能在系统里看到TA的小传资料,介绍TA是谁,为什么会来这里。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里没有工具人,即使是配角也获得了包容和关怀。
《环球人物》:在关于游戏的讨论中,“文化自信”高频出现。您怎么看?
白惠元:我认为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主体性,就是我对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信心,所以我邀请你进入我的文化逻辑,而不是我非常焦虑地要加入你的世界。
我想到了2002年的电影《刮痧》。片中的男主角是一名移民美国的游戏设计师,他将游戏主角设定为孙悟空,因为这是中国的传统英雄,正义、善良而有道德,可美国律师指责孙悟空顽劣粗鲁,有暴力和虐待倾向。这一文本的时代语境,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希望得到世界或者说西方的认同。
22年过去了,电影中的部分情节在现实里上演,不同的是,《黑神话:悟空》成为中国游戏走向世界的代表。从默认语言设定为中文到依据原著的各种细节取材,都是一种主体性非常鲜明的表达,它首先要让中国玩家满意,再考虑其他群体。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表情包,就是8月20日玩家心态:国内玩家放飞自我,国外玩家研读《西游记》原著。这背后的意味是,我们邀请你来一起重访中国传统文化,邀请你加入我们的世界——你不理解,我不怕;你能理解,那就更好。
在这个分众时代,《黑神话:悟空》似乎又让我们感受到了难得的大众时刻:朋友圈里的玩家们“异地同时”玩游戏,并更新过关进度。“想象的共同体”的召唤媒介曾经是报纸、小说,后来是电影、电视,现在是游戏了。
《环球人物》:最后,孙悟空的前世今生,可以给我们何种启示?
白惠元:我们有必要在全球化的语境内,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代价值。正是一代代创作者的跨媒介“文化转换”,使得孙悟空形象具有了一种文化记忆的层累效应。这位神话英雄得以从古典名著中走出,闯入现代,并在不断的“变形”中,成为变革时代的见证者。
 责任编辑:邱小宸
责任编辑:邱小宸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要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