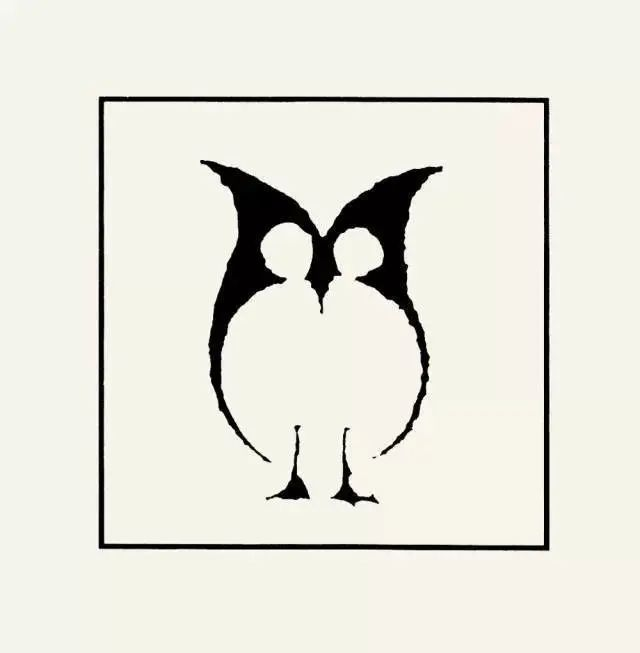1923年8月3日,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录了《狂人日记》《故乡》《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名篇。
时至今日,《呐喊》已出版100年。小说中的人物和话题,“救救孩子”、闰土、阿Q精神、人血馒头、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不仅成为经典的文化符号,且仍在当下被反复提及、讨论。
百年间,鲁迅的形象,也经历了几次颠覆性的重写:从“民族魂”的崇高象征,到“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中学语文魔咒,再到今日的“网红”“顶流”——神坛上的文学宗师,“下凡”得彻底。
鲁迅在年轻人中有多火?《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显示,《鲁迅全集》是“95后”最爱的文学读物。他是B站上最火的文豪,在微博上拥有自己的“超话”;他的《野草》 被北大学生改编成说唱歌曲,他的《故乡》演绎出“当代聊斋”《闰猹抄》;他说过的、没说过的话,被做成表情包四处流传;《觉醒年代》热播后,鲁迅“不干了”的立牌,被打工人虔诚地供于工位……
从“最怕周树人”到“迅哥儿永远的神”,在中文互联网的世界里,鲁迅何以吸粉无数?而在语言狂欢之后,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鲁迅的精神遗产?
宝藏男孩/斜杠中年
如果说,“官方鲁迅”“学界鲁迅”和“教科书鲁迅”塑造的是一个“大他者”“大权威”,那么“互联网鲁迅”,则带来打破刻板印象和权威塑造的巨大快感。网友们在文本的犄角旮旯,在“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定义之外,重新挖掘鲁迅身上的多元化与草根化。
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最具原创思想价值的作家,无疑是座“富矿”,越挖越有料。
论文化修养,鲁迅是跨界KOL。
他懂德文和日文,英文能读一点点,一辈子翻译了近百个作家的作品,比自己写的东西还多。
他的古文功底深厚,《汉文学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可见修养与见识,绝不是文人玩票的学术书。
他是冷门知识博主,从士大夫遗忘的文献里抄录了许多罕见资料。比如《岭表录异》,专记广东风土物产,没有道学气,文人本真的东西流于其间。
论艺术审美,鲁迅是直男翘楚。
他是古代艺术收藏家,对汉代画像石情有独钟,搜购了5100多种,线条朗健、构图灵动,充溢汉唐气象。
他是新兴木刻发起者。当国内艺术大师、美术院校对木刻不屑一顾时,他拿出珍藏的原拓当教材,举办讲习班。鲁迅去世后,哭得最痛苦的是木刻青年,多年后,他们在抗日战争宣传中,擎起耀眼的艺术火把。
他是资深影迷,战争、爱情、奇幻、歌舞、侦探、悬疑、动画……都能欣赏,有时还二刷、三刷。
他是设计大师,设计了北大校徽,以及自己60多个书籍封面。
有时也手绘,画他最喜欢的猫头鹰。
及至日常穿搭,也颇有心得。自己不讲究,但愿意指导别人(比如萧红)。他有一张照片,渔夫毛衣开衫、V领毛衣、中式立领衬衫,毛衣塞到裤子里,可见一旦想起来拾掇自己,也是“时髦精”。
这样一位“斜杠中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互联网原住民们的理想镜像——拥有“不明觉厉”的技能点,也不乏“深接地气”的兴趣圈。
他们进而发现,这个百年前的“宝藏男孩”,也经历过自己当下的生命体验。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第二天住进了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被34只臭虫赶到桌子上睡了一夜。白天,他去教育部上班,“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晚上听着福建来的邻居“大嗥如野犬”,平时以抄古碑、辑古书、读佛经的方式消遣度日。夏夜便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一只壁虎,被他养在小盒里,每天喂稀饭,养得又胖又大,人来了也不逃走。
此时的鲁迅,还不是那个随《狂人日记》登场的名人。吃不起广和居的烩海参、烩鱼翅、糟熘鱼片,只能吃些熘丸子、炒肉片之类的廉价家常菜;常常嘴里“淡出个鸟来”,动辄饮于酒馆;他喜欢稻香村的萨其马,曾站在北平的街头大吃葡萄,夜里写完两封信、吃了三个梨,还要在日记里感叹一句“甚甘”。
此番情景,与今日的“北漂”“沪漂”“深漂”何其相似——白天打工人,回家撸宠物,点外卖盘算着价格,也享受日常生活里的“小确幸”。
32岁的落寞北漂、45岁初恋的“情书大王”,50岁的宠娃狂魔老父亲……一个作为“普通人”的鲁迅,穿越民国历史现场,开始与屏幕前的网友产生心灵共振。那份生命的热力,击打着每一个“未老先衰”的赛博冲浪人。
1936年,鲁迅的身体日渐衰败。6月后,更是几乎逐日接受注射,间断地发热、吐血。8月25日,鲁迅得到曹靖华寄来的“猴头菌四枚,羊肚菌一合,灵宝枣二升”。两天后回信:“红枣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得,羊肚亦作汤吃过,甚鲜。猴头闻所未闻,诚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但我想,如经植物学家及农学家研究,也许有法培养。”再过11天又写信,还是津津乐道:“猴头已吃过一次,味确很好,但与一般蘑菇类颇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名字。”
这年10月,鲁迅只活了19天,却去剧院看了3部片子。最后一部是《复仇艳遇》,喜欢的不得了,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发着高烧还写信向朋友推荐。
他为每一个中国人示范了,如何畅意从容地面对生死。在此意义上,“鲁迅确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喜怒哀乐与共”。
“梗王”与“嘴替”
相比鲁迅其人,他的文字,更全面地参与了当代年轻人的日常世界。
鲁迅的文字,嬉笑怒骂、颠覆常规,极具“网感”,被网友称为“亚洲第一梗王”。
有时很“无厘头”。他写过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调侃徐志摩等人动辄“阿唷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
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有时很“恶趣味”。《故事新编》里有篇《奔月》,讲后羿箭术太好,最后没有大兽可以射,就去射乌鸦,给嫦娥做乌鸦肉炸酱面,天天吃天天吃,嫦娥生气了,就独自奔月了。
有时很“恶趣味”。《故事新编》里有篇《奔月》,讲后羿箭术太好,最后没有大兽可以射,就去射乌鸦,给嫦娥做乌鸦肉炸酱面,天天吃天天吃,嫦娥生气了,就独自奔月了。
有时兴起,也想做做“同人文”。他对郁达夫讲,自己想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
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也许是授意军士们的。
相比陈凯歌的《妖猫传》,鲁迅的《长恨歌》故事,暗黑得更有意思。
在某种程度上,鲁迅深深打入了互联网语言的基层结构,那种独特的个性、深刻的简洁、犀利的谈锋,是新媒体时代理想的传播范式: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网友们继而开始模仿“鲁迅体”,书写各自五味杂陈的生活:
我大体是病了,知识在眼前,却被脑袋拒之门外。
我翻开工资单一看,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了“事多钱少”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整本工资单只写了两个字——走人!
我在职场中,常发现当面称我为同事的,暗中却将我做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
在讨论社会热议话题时,鲁迅也常常成为“互联网嘴替”。
谈“男女平等”,鲁迅说:
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谈“键盘侠”,鲁迅说: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
谈“家庭教育”,鲁迅说: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谈“造黄谣”,鲁迅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谈“佛系青年”,鲁迅说:
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
这些“鲁迅说”,被网友视为社会批判的“元语言”与“终极真理”,却也反衬出面对复杂的社会肌理,当代人日益疲软、匮乏的思考与言说能力。
在狂欢的玩梗与表层的援引之外,鲁迅于我们,还意味着什么?
“我们都是闰土、阿Q、孔乙己”
继承鲁迅最好的方式,是进入他的文本。
很长一段时间,提及《故乡》,“互联网乐子人”想到的,第一是某位冠名于“闰土”的男歌手,第二是“瓜田里的猹”,形容八卦太多,一时看不过来。
但在新的境遇下,《故乡》再度将读者卷入,用文字映照他们的现实,宣泄浓重的无力感:“小时候读《故乡》,对长大后的中年闰土是看不起的,可等我们自己成了大叔,像所有普通人一样背上生活的重担时,再回首,原来自己终于成了闰土。”
如《故乡》一样,当年那些刻板记背的鲁迅文章,如今读来,有了特殊的况味。
“在计划裸辞再想到房贷孩子后说‘算了算了’时,脑海里冒出一个熟悉的身影——阿Q——那个一边自我矛盾一边自我安慰的人。那一刻我无师自通了社畜们的‘精神胜利法’,于是又能笑着迎接明天。”
“最开始读孔乙己的时候,我是那个柜台后的小柜员,我嘲笑孔乙己冥顽不化、自讨苦吃;毕业后再读孔乙己,我是那个酒店老板,我不关心孔乙己,我只记得他欠了我九个大钱;经历社会锤打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才是孔乙己,我唯一拿得出手的不过是茴字的四种写法,可那成为了我被嘲笑的源泉。”
如此才发现,鲁迅写《呐喊》,并非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国民性批判,将闰土、孔乙己、阿Q痛贬一通了事。人之所以成为奴隶,往往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多重因素的压迫,如鲁迅所说,是“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他更将自己放入这可悲可鄙的小人物序列——在某种程度上,孔乙己是他的过去,假洋鬼子则是他的现在。
100年过去,今天的读者从这些故事中,看见了命运的交叉。时代在前进,却并不允诺“黄金世界”的必然到来。当年,鲁迅写下孔乙己等人的故事,揭开东方铁屋中反复上演的狂热与麻木、奴役与压迫,自己也陷入思想的缠斗,在怀疑与悲观中无法自拔。最终,他没有沉沦其中,以满腔的热情洞穿黑暗和虚无,以绝望的抗争摆脱冷气与鬼气,不靠天、不靠地,不惮中伤、不惧孤独、不屈服于敌人、也不盲从于战友……
在此意义上,脱下还是穿上长衫,并没有唯一答案。你问鲁迅,他会说: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挡)。
年轻人为什么喜欢鲁迅?知乎上有一个回答:他到死都没变成一个倚老卖老、老气横秋、胆小怕事、装模作样的老油腻。
《热风》随感录中的这段话被广泛援引: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真正走进鲁迅,要我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要时时自省:不要变成一个保守、驯服、崇拜权力、贬抑弱者的“看客”,不要沦为一个头脑机械、思路狭隘、总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新愚民”,不要陷入对空洞名目的崇拜和迷信,成为被端上席面的“醉虾”。
这样的人生,当然不是容易直面的,但这正是鲁迅选择的道路。
30年前,学者王晓明写了一本《无法直面的人生》,那是一本侧重表现鲁迅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剧的传记。序言中,他写道:
一个人要直面人生,也须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这直面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等待无可延宕的毁灭——你还能够直面吗?不幸的是,鲁迅恰恰遇上了这样的人生。我甚至想,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