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双雪涛参加《飞行家》路演活动。
小说家双雪涛最近忙了起来,向来低调的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同步上映,一部是《飞行家》,一部是《我的朋友安德烈》。两个不同的故事,但主角都是“异人”——《飞行家》里的下岗工人李明奇,热衷造飞行器,想飞上天;《我的朋友安德烈》里的安德烈有点儿天才有点儿傻,读中学的他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试图推翻数学定理,在升旗仪式上演讲《下水道井盖为什么是圆的》……


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双雪涛的小说很难被改编成电影,因为他的作品之所以戳中人心,更多的是文字本身、人物刻画、气氛烘托,以及似有似无的阴郁和忧伤。近年来,他的小说屡屡被改编成影视剧,从电影《刺杀小说家》到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等,均引发热议,但有的叫座不叫好,有的叫好不叫座。这一次,人们的好奇心再次被勾起:这两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后会变成什么样?
人民文娱记者曾经两次采访过双雪涛,和他谈论作品、写作经历、人生变迁,也谈论电影。就在两年前的那次采访中,他说:“电影只是兴趣,写小说是职业。”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写作对他来说是可以独自完成、全盘掌控的——这是他一直写作的原因,也是他面对世界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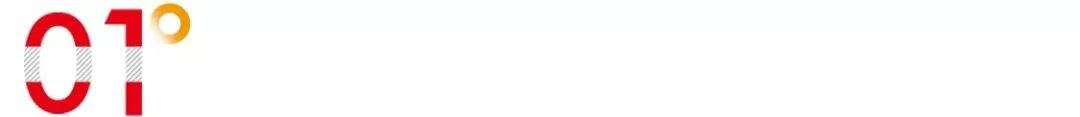
再跳一次,重新开始
电影《飞行家》讲的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有些荒诞和浪漫:东北“犟种”李明奇(蒋奇明饰)和他的妻子高雅风(李雪琴饰)如何用一辈子的时间,守护一个“飞上天”的大梦想。

整个故事跨越半个世纪,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26年,主角李明奇经历了3次飞行:第一次为自己纯粹的梦想,带着年少意气的执着,也是对父亲未竟梦想的延续,最终因意外事故戛然而止;第二次是为了生计,工作丢了后开舞厅,靠放飞热气球为舞厅宣传造势,藏着中年男人向现实妥协的无奈;第三次则是为了希望,为拯救侄子、捍卫尊严,他明知上一次失事的悲剧历历在目,仍选择义无反顾为之一搏,从599米的高空一跃而下。

3次飞行串联起李明奇的人生轨迹和心路蜕变,同时也映射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落寞与社会转型阵痛。电影中,雪花膏、迪斯科、波浪大卷、歌舞厅等,处处都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生于沈阳的双雪涛,从写作那一刻起就在书写时代,但又不止于此。沈阳的寒夜、钢厂、烟囱与童话的翅膀,艳粉街、影子湖、光明堂、红旗广场,普通人生存的困顿、人性的深渊、命运的捉弄,都被他塞进了自己的故事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曾评价说,双雪涛的书写将笔尖伸向更广阔的历史,然而却不停留于历史事件的复刻,“他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回到现实的的生活之中,思考尊严、命运以及我们与生活的关系”。
电影《飞行家》拍的,从来也不只是“飞行”,而是每个普通人,在漫长琐碎的生活里,寻找自己“精神终点”的跋涉。在片中,李明奇曾跟小舅子描述自己的远大梦想——“我不用飞多高,三四米就行,人飞高了,看世界不就变了,脑子变了,那世界就变了。”

作为《飞行家》的监制、编剧,双雪涛“希望观众看完能有像洗温水澡或热水澡的感觉,从里到外被涤荡”。在小说中,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

1月16日,双雪涛跟着《飞行家》到华东师范大学路演。主持人毛尖问他:“《飞行家》是要给2026年的观众一个精神重新投胎的机会吗?”双雪涛笑了笑,答道:“我们也希望这部电影能给观众一次精神上重新出发的可能。”

“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
2011年,双雪涛就职于一家省级银行,白天上班,夜晚写作。偶然一个机会,写下处女作《翅鬼》,得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在这个奖的鼓励下,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上班时继续贴汇票、做报表、整理档案;下班后则戒了喝酒和应酬,天天在电脑上敲字写小说。

第二年,双雪涛拿到了台北资助作家创作长篇小说计划的项目入选通知。他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这辈子到底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担负起写作的责任,跟一眼可以望到头的银行职员生涯做一个决裂?7月的一个早上,他冲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辞职,走上了专职写作的道路,每日写作、读书,不虚掷光阴。之后,他的作品逐渐在《收获》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引起评论家与读者关注。
真正让他找到写作感觉的是短篇小说《大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棋艺超群的下岗工人,原型来自他的父亲。父亲聪慧过人,打小就是数理化尖子,后来赶上上山下乡,在农村没有什么消遣,只能看书和下棋。下得多了,他便成了一个棋痴,连炒菜时也常常一手颠勺一手拿着棋谱。
在这篇小说中,双雪涛将自己最为熟悉的语言——东北话,融入叙述中,字里行间夹杂着东北人特有的自嘲、幽默,以及残酷和决绝。而这种语言风格日渐定型,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了2014年,双雪涛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磨出了一部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他从自己少年时的东北记忆入手,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大工厂,“那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但这段历史就这么被搁置着,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
他以工人子弟的身份讲述着父辈下岗工人那一代的故事,小说由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陈年往事——艳粉街的少年成为刑警,负责侦查12年前的旧案,嫌犯渐渐指向儿时邻居家的父女,刑警深陷其中,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参与者……小说发表后,一片叫好,双雪涛也真正走入公众的视野。
“《平原上的摩西》是我的幸运之书。我后面一直在写作,包括《飞行家》《猎人》《聋哑时代》,到最新的《不间断的人》,才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双雪涛说。

· 双雪涛参加《平原上的摩西》读书活动。
确实如此。《平原上的摩西》带着双雪涛走出艳粉街,走出沈阳,走向了更大的世界。这部小说出版的2016年,几乎大半个文学圈都在谈论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坛新秀。这一年,他陆续出了3本书,除了《平原上的摩西》外,《聋哑时代》《天吾手记》都是积压了4年的旧作,奖项也纷至沓来。第二年,他又推出小说集《飞行家》中,将目光对准那些渺小的边缘人:有失败的小说家,枉死的工厂主,沉溺幻想的小职工,落魄潦倒的写手,被遗弃的孩子……
由于他一直以工业城市中劳动者的命运为书写对象,文字语言也带有一种工业感,很多人将他归到东北写作的体系里。
但双雪涛本人不这么认为,“我并不是只写东北。我只是借用东北的一些素材,来写人和人性。艳粉街早已经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经模糊。”他说,小说永远代替不了历史,他的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而不是真正生活的历史。

人生的中缝
人民文娱记者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采访双雪涛时的情形。
那是7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参加百花文学奖的活动——作品《平原上的摩西》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活动后,我们在一个快餐店里聊天,聊写作、个人经历和新作《飞行家》。当时的他,已到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进修,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一直没完结,便把胡子留了起来,“不写完不剃”。而胡子之于他,还有另一层意义:克服不安感。这种不安,既源于从沈阳到北京、身处异地的不适和紧张,也源于成名后站在聚光灯下、立于人群中的无所适从。
“写作搭救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了另外一种人,让我有了另外的一种人生。要不然现在还在银行上班,还困在一个孤岛上,就像突然来了一条船,把我接走了,然后自己划一划,发现还有这么广阔的世界。”双雪涛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当困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时,他找到了写作;当写作和思维被“东北”“父辈”“历史”等罩住时,他来到北京,渐渐稳当下来,有了一种“可控的、恰当的自由”。
这些年,他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最新小说集《不间断的人》,是他迄今为止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从2019年到2024年。这5年,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泛滥等,他不断地对自己原有的想法产生质疑,甚至一度陷入悲观。在悲观的情绪里,他写《淑女的选择》,借“星期五女孩”的口说“互联网毁了文学也毁了这个世界”;写《刺客爱人》,呈现凶杀案背后善与恶的纠葛,探讨碎片化、分裂的世界人对欲望的控制;写《爆炸》,关注网络暴力……

“可以说,这是互联网社交媒体深入发展的时代诞生的一个小说集。”双雪涛如是定义。在他看来,社交媒体拓宽了一部分人的暴力感的边界,也让不少人倾向于痴迷娱乐性的东西。“幸而有写作、有文学,文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让人更像人。文学处理的问题都是‘人为什么成为人’。”
跨过40岁的门槛之后,双雪涛突然意识到已经来到了人生的中缝。有一次,他因为运动受了伤,做了个小手术,膝盖里还曾打了几个小钉子,“这可能也是中年身体的一个反应”。之后两个月,他没有运动,感觉身体也停滞了下来。
同样感到停滞的,还有心理。有一天,他发现现在流行的APP,如小红书、快手、抖音,他的手机上一个都没有。“我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新一代年轻人已经有了挺明显的区别。”对一些原本笃定的事情,他也开始有所怀疑。
“这样的年龄,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自己?”记者问。
“调整心态。一方面承认自己年龄上来了,要注意;另一方面,尝试与一种悲观的情绪共存。”双雪涛说。
他不太比较过去和现在,也不需以此自我检查和反思。“我的变化?不需要我来说,读我小说就可以,应该是你们(读者)来做的事儿。”他笑着说。小说家赵志明曾评价双雪涛“天性幽默,敢于自嘲,一件寻常的事情由他说来便也舌灿莲花”。但这仅限在熟悉的人面前。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受访者,他一直自我警惕,不喜欢多讲自己。即便坦诚地完成一次采访,真正的、表面上微社恐下的另一个热烈的双雪涛,依然只藏在作品里,在细小与幽微处,冷着眼,揣着心里那团火。
这几年,双雪涛结交了一些影视圈的朋友。最常聚的也就六七人,大都是合作过的导演、编剧,常常结伴一块去涮肉馆,热腾腾的羊肉就着啤酒吞下去,不聊闲篇,就聊电影和文学。也有些作家转行做电影,但他没动过这个念头,“我不行,一看人多就紧张……还是自己待着写小说吧。”
双雪涛向往的生活,就像他一直以来的偶像村上春树那样——村上辞职之后开了家小店,边开店边写小说。双雪涛也过着简单的生活,早起写作,下午出去散步、踢球——最近因为手术停了下来。晚上想办法改一改白天写的稿,如果不行,就看电影、看书、睡觉。
“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阅读者,一个胡思乱想的赋闲者,与世界的联系就是在独自一人坐下的时候。坐在一把枯燥的椅子上,看着一个个人物和故事生长出来,是一件快乐的事。”他说。
 责任编辑:高玮怡
责任编辑:高玮怡双雪涛
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要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