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赵毓龙在沈阳参加中国俗文学学会2023年年会活动。
赵毓龙
1984年出生于辽宁丹东,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与戏曲研究,尤以《西游记》成书与经典化、西游故事跨文本演化传播等研究见长,著有《中国古代小说简史》《破顽空:西游知识学》等。近日出版《花窗三十看“西游”》,引发关注。
2025年是一个“西游盛年”。
年初第一波文旅热,是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带火的山西古建——春节期间,隰(音同习)县小西天不足200平方米的大雄宝殿里,1978尊悬塑佛像每天要接待上万游客;暑期档爆款,是打破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纪录的《浪浪山小妖怪》——西游故事里充当“背景板”的小猪妖踏上取经路,另一种视角,全新的故事;连话剧舞台上,演的也是取经路上的事儿——话剧《太白金星有点烦》让“龙套配角”太白金星从天庭神仙变身职场打工人,直击当下痛点,被观众称为《西游记》“灵魂续作”……

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孙悟空。(视觉中国)
“‘西游IP’在四大名著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我们发现,不管改编作品如何偏离原著主旨和风格,只要自圆其说,受众都会喜欢。”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毓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过去近20年间,他都在与《西游记》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缠斗,从在辽宁大学读研,被导师拉上《西游记》的“贼船”,到返校任教成为说西游的“讲台男神”,从学术上的阅读研究到科普向的写作与传播,《西游记》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要翻越的灵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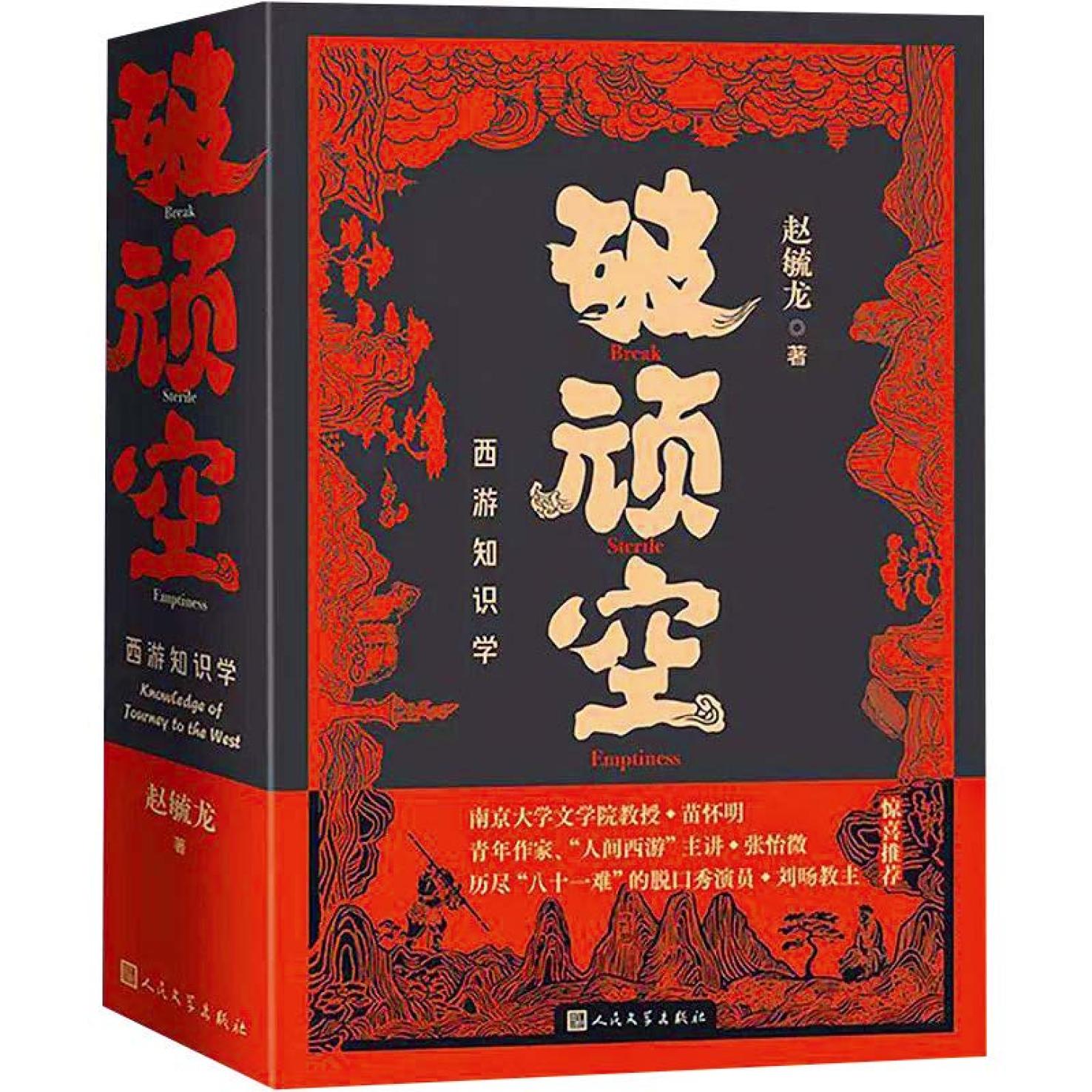
赵毓龙的著作《破顽空》。
2025年,也是赵毓龙集中输出“西游”的一年。他开播客、录课程音频,在网络平台收获大量听众;又出版《花窗三十看“西游”》《破顽空:西游知识学》等著作,奔赴各地与读者交流,帮他们拨开刻板印象的迷雾——“看见”取经“五圣”的形象演化、因缘关系、前世今生,“看见”神魔的盘算与顾虑,“看见”小妖干脏活的日常,“看见”自己,也“看见”众人。
关于“攀登灵山”过程中的见闻与思考,可讲的实在太多。以下是赵毓龙与记者的对话。
“一个都不能少”
《环球人物》:近些年您不断输出对《西游记》的解读,《花窗三十看“西游”》等作品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赵毓龙:最近经常和同事、朋友开玩笑,说自己终于“踩在风口上了”。近年来,西游故事在多媒介、多领域被改编、重塑,各种作品密集地出现,并且都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我看来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同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没有读过《西游记》原著。很多人通过电视剧、电影、动画、动漫、游戏等各种媒介和渠道看西游,对其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场面也都非常熟悉,但那是由跨媒介“二次叙述”构建起来的笼统印象。相比而言,阅读原著是另外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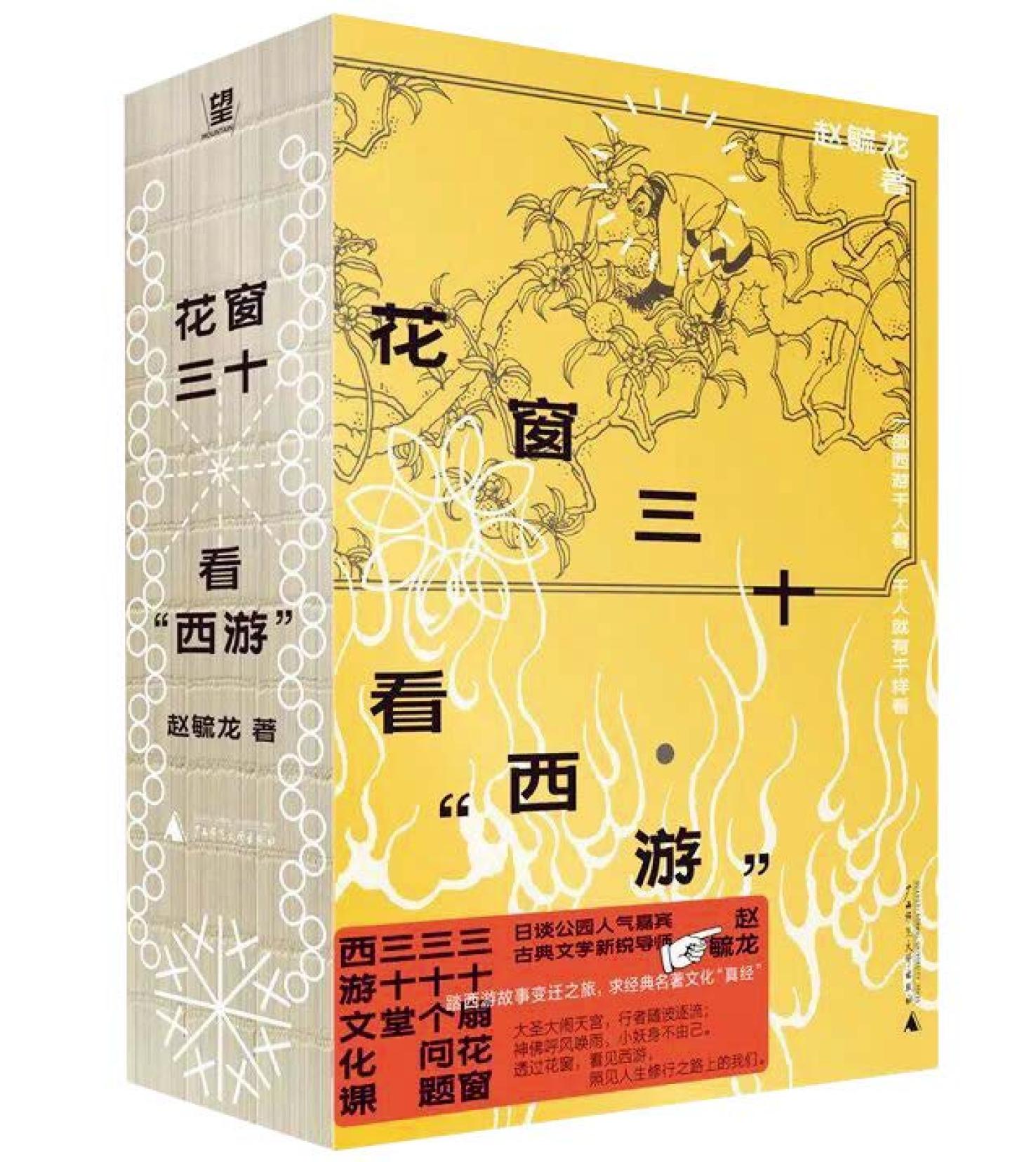
赵毓龙的著作《花窗三十看“西游”》。
《花窗三十看“西游”》的创作初衷,就是希望带领感兴趣的读者,回到《西游记》原著,重新聚焦这个庞大、繁复、魅力无穷的文学景观。
《环球人物》:原著里,西游“五圣”是读者最关注的话题,您在书中分别用“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来区分八戒、唐僧、悟空。先来说说“超我”孙悟空,他经过了哪些演化、改写,才有了如今的超我性?
赵毓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像经常有读者提出:百回本《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为什么前后明显不一致?“大闹天宫”的悟空,具有极强的叛逆性、抗争性,武力值超群;“西天取经”的悟空,则表现出较强的归化性、虔敬性,武力值也明显降低,经常斗不过魔怪,无论是对付民间野生者,还是私逃下界者,常常需要外援支持。
其实,这一现象是可以解释的——从形象演化历史来看,两者本就来自不同原型。“大闹天宫”的猴王表现出明显的妖性,是因为其原型取自中国古代的本土猴王,以福建的最为著名,福建猴王形容凶恶,属于“恶相”。而“西天取经”的猴王形象,一部分源自印度神猴哈奴曼。在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聪明勇敢、善于变化的哈奴曼帮助罗摩打败魔王,解救了他的妻子悉多,表现出礼敬、虔诚的“善相”。《罗摩衍那》的故事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哈奴曼与本土猴王融合,形成了百回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这是一个经过提纯、净化的形象,它剥离了很多杂质,因此具有超我性。
《环球人物》:反观八戒,他是《西游记》中代表“本我”的最典型角色,您提到他也是故事的灵魂人物,为什么?
赵毓龙:许多人儿时读《西游记》,大都咒骂过猪八戒,厌恶他自私懒惰又好色,埋怨他拖孙悟空后腿,尤其读到猪八戒撺掇唐僧念紧箍咒时,更是对他恨得牙根儿痒痒。然而,如果把猪八戒的情节从书里整个剜掉,取经路上顿时就少了很多欢声笑语。当我们日渐成熟,学会与现实世界妥协,并与“不完美的自我”达成谅解后,更会发现:我们其实并不讨厌猪八戒,恰恰相反,觉得他可怜又可爱。八戒固然贪吃好色,但“食色,性也”,即便实现了社会化,这依旧是我们的本能。八戒固然贪财,但对于财富的渴望,不正是相当一部分人乐于持续努力的主要动力吗?
同样的道理,作为“自我”象征的唐僧,代表理性和常识,处于“自我”与“本我”的张力之中。所以,当我们看他面对女儿国国王“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抬头”时,是否也忍俊不禁呢?
而整本《西游记》,如果没有爱和稀泥的沙僧,没有八戒与悟空的相爱相杀,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成色吗?就连“五圣”中存在感最弱的小白龙,不要忘了,他也是取经人的徒弟,最后修成“八部天龙马”……所以,西游“五圣”一个都不能少,是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特质赋予了西游故事以迷人的光泽,为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
配角们的日常
《环球人物》:除了“五圣”,这些年大家越来越关注《西游记》中的配角,比如小妖怪们,您怎么看待这些角色?
赵毓龙:与西天路上的大魔头比起来,形形色色的小妖更容易引发当下人共情。他们大多没有吃唐僧肉的幻想,只是受大妖魔差遣,完成日常的琐碎工作,跑腿、报信、抬轿、打扇、烧火、做饭,给野兽剥皮放血、清扫魔窟窑洞里的血腥渣滓……许多有名的小妖,比如精细鬼,狮驼岭的小钻风、奔波儿灞、灞波儿奔……以及千千万万不具名的小妖,都过着这种干“脏活”的日常。

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剧照。(片方供图)
我们共情小妖怪,是把自己代入了他们的生活,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由此,我们忽略了他们作为坏人帮凶的身份,在其“无辜”惨死时,为其感到难过,甚至抱不平。这实在是一种自我感动、自我陶醉。我想说的是,与其在虚构的通俗文艺中寻找廉价的自我认同,不如在现实生活中用心观察一下做“脏活”的人,倾听他们的心声,以此来分担其承受的生理与精神压力。
《环球人物》:百回本《西游记》中的神祇形象也很有意思,他们的塑造有什么特点?
赵毓龙:符号化的神祇人物,只能在叙事上完成功能,却不能在文学上打动人。所以,百回本《西游记》解构了神祇的崇高感。比如第九十八回,迦叶与阿难公然索贿,就是绝妙的嘲讽。在历史真实中,迦叶与阿难是释迦牟尼的长随侍者,修成正果之后,地位也格外崇高。进入小说,他们唯利是图,甚至仗势欺人。以点带面,可以想见灵山上的四金刚、五百罗汉、三千揭谛、十一大曜、十八伽蓝,都是怎样的嘴脸。
这便是写定者笔下的神祇,脸上或多或少都有杂色油彩,以至山根不正,眉眼乜斜。如此一副尊容,怎会令人心生敬畏?
灵山只在汝心头
《环球人物》:总有人说,四大名著里《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是我们看到,它拥有庞大的受众,而且一部又一部“二创”作品层出不穷,这股生命力从何而来?

1986版《西游记》剧照。(豆瓣电影)
赵毓龙:小时候,我也像大部分“80后”一样,通过1986版《西游记》了解取经故事,家里的四大名著是被锁在书柜里的——父母觉得你还不到时候看。当我长大一点再去读原著时,觉得小说写得没什么意思,跟电视剧比它不过瘾。后来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有了些文学素养,年龄也到了,原著的妙处就品出来了。
西游故事强大的生命力,用今天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IP。文学经典大致分两种,文本IP属性特别强的,典型代表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极高,但它会束缚当代改编者的手脚;另一种是故事IP,像《西游记》《封神演义》,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故事,至于故事怎么讲,全看你的本事。你可以写一个黑化的孙悟空,可以让御帝哥哥动真情,可以进一步抹黑矮化天庭、灵山上的大佬,也可以给西天路上的魔怪单独开支线……这就是西游宇宙,反复地折叠它,我们总能看到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
《环球人物》:从青年时代读研开始,您做西游研究近20年,如今为何还有热情?
赵毓龙:回想起来,以《西游记》为研究主业,其实是很偶然的。我本来对《金瓶梅》《红楼梦》很感兴趣,《西游记》“无可无不可”,研究生面试时,辽大文学院院长胡胜教授说,“感兴趣的拿来做研究,就连兴趣都没有了”,于是《西游记》这座山就落在了我面前。这样走了小20年,师父从没生过退悔心,我也从没生过退悔心,因为登山并不枯燥,一路攀登,其实也是在行玩光景,听一听鸟叫,吹一吹风,拾一片树叶看看,摘一只果子尝尝。
我们都有自己的山,山头总是很遥远。借悟空的话,所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又所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包括治学在内的所有修行,只要心里笃定,放开怀抱,一路登上去便是,最后登到哪里,哪里就是山头。
《环球人物》记者 高塬
 责任编辑:蔡晓慧
责任编辑:蔡晓慧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要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