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小时候学语文,都听过“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在这“三怕”里,可能又数周树人让人犯难。鲁迅的文字不仅文白交杂、不时穿插方言,更重要的是往往联系着他当时当刻的思想与情绪。理解鲁迅写作的“语境”,才是走进鲁迅文字的钥匙。
“重新理解语文课”专栏来到了第10期。彪老师说,她最近正好在讲鲁迅的《藤野先生》,鲁迅在这一名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在这段至关重要的日子里,鲁迅与藤野先生的交往,在思想层面也发生着“弃医从文”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古今中外既有的研究、历史记录已有很多。但彪老师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对这种转变产生“同情之理解”。
语文课上,讲完了《藤野先生》中的核心事件,我问了学生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给这篇文章重新拟一个名字,你觉得还可以叫什么?”
我请学生将讨论后的答案写在黑板上,很快,黑板被他们写满了各种奇思妙想:
《我在仙台学医的日子》《仙台回忆录》《重生之我在日本弃医从文》《回忆我的恩师》《藤野严九郎二三事》《我的解剖学老师》……
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这篇回忆性散文中,除了记述了我和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还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记录“我”的求学经历和人生选择,这也就是教参上所说的“明线”与“暗线”交织。黑板上学生的答案一眼看上去五花八门,但仔细一看,就能发现学生已经读出了这篇文章的双线结构:
《回忆我的恩师》《我的解剖学老师》等题目关注的是本文的明线,也就是“我”和藤野先生的交往;《我在仙台学医的日子》《仙台回忆录》《重生之我在日本弃医从文》等题目则关注到了文章暗线,也就是“我在异国他乡逐渐觉醒的心路”。
可见同学们已经感受到,这篇文章不只是纪念一位老师,而是在回答“周树人怎样成为鲁迅”的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把《藤野先生》当成鲁迅自传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给同学们展示了《朝花夕拾》的目录及其写作时间,问大家:“你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作者供图。
学生看着这份创作时间表,一开始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无非是一两个月写一篇。但当我把《父亲的病》《琐记》和《藤野先生》圈起来时,学生终于惊呼:“这三篇几乎是一周内写完的!”
这三篇讲了什么呢?讲的就是鲁迅为何想学西医,如何去南京、去东京、去仙台,如何决定弃医从文的故事: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
——《父亲的病》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啰,普弥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琐记》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藤野先生》
读过这两篇文章之后,我们就能理解《藤野先生》开篇的那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实则是起到了承上之“荒诞”启下之“无聊”的作用。见过了给蟋蟀配对的庸医,见过了和尚放焰口的荒诞,紧接着还要见识清国留学生在樱花树下的丑态百出。可想而知,周树人同学心里的失望已经层层累积到了什么地步。而这时,一个颇严谨、又颇热心的藤野先生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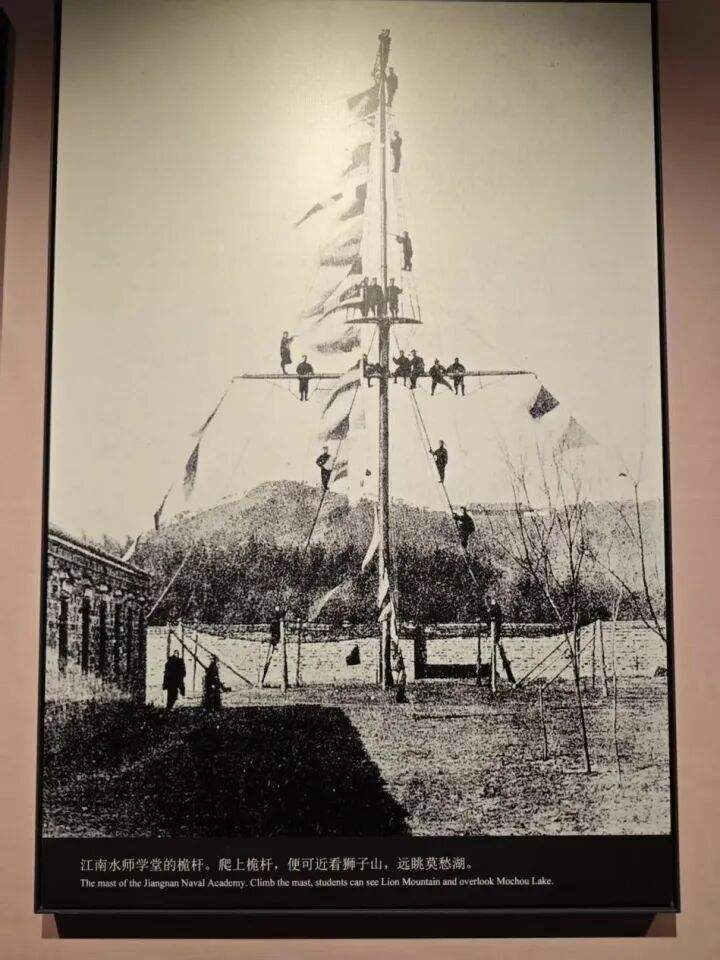
作者供图。
脱离《朝花夕拾》的前后文,很难理解藤野先生对于日本留学时期的周树人的重要意义。当他一路“走异路、逃异地”,见识了许多落后的人,更见识了许多看似进步实则迂腐的人之后,有一个挟着一大摞大大小小的书的、有些古板又有些拘谨的、颇有学究气的教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万幸,世界这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里,还有一个藤野先生。
在仙台的那两年,鲁迅并不只是学习解剖学和临床医学。除了课堂与实验室,他也频频出入留学生聚会、文社活动,与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相识,其中就包括后来为革命牺牲的秋瑾。那时的仙台并非政治中心,却是一个思想暗流的交汇处。周树人通过《浙江潮》等杂志接触到了民族启蒙与救亡图存的议题,也正是在此期间,他的民族意识从模糊的忧患感转向了更清晰的反思。最终,在“匿名信事件”和“幻灯片事件”的催化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与藤野先生告别。
写到与藤野先生告别,这篇文章的“明线”与“暗线”汇聚到了一起。
为什么鲁迅没有把文章写成《藤野严九郎》《我的解剖学老师》?
学生自己便知道:因为那样太“单薄”了。
那样的标题只停留在人物传记或职业关系的层面,无法承载“精神启蒙”的意味。“藤野先生”对于鲁迅来说,不只是一个“教授解刨学的人”,不只是一个“关心学生的人”,甚至不只是一个“有学术情怀的人”,更是一个行事风格和理想追求都在那个秩序混乱的环境下显得“认真”过头的人。
所以,当我们把《父亲的病》《琐记》与《藤野先生》并置,看到的不仅是一周内完成的创作奇迹,更是一部浓缩的、充满张力的自我宣言。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从传统与现实的荒诞中突围,如何在人生的“米”字路口中寻找坐标,并最终确认了塑造自己的核心力量的过程。藤野先生之于鲁迅,已不仅是一位恩师,更是黑暗中的持微火者。
而当鲁迅在1926年于厦门重写这段往事时,经历着“女师大风潮”后的纷扰与孤寂,独居于鼓浪屿。北伐军正席卷全国,革命的口号此起彼伏,但他眼中的中国依旧充满麻木与暴力。四十六岁的他,已经历了朋友的离散、学生的误解、舆论的围攻。写藤野,不仅是对一位恩师的怀念,也是对“认真”和内在秩序的召唤,他在反复讲述和确认:我是如何一路走来的,我要如何走下去。
于是,学生那个看似戏谑的标题《重生之我在日本弃医从文》,未尝不是一种理解本文的可能:那个在混乱教室中做出的决定,确乎是一次“精神重生”。
 责任编辑:蔡晓慧
责任编辑:蔡晓慧鲁迅,《藤野先生》